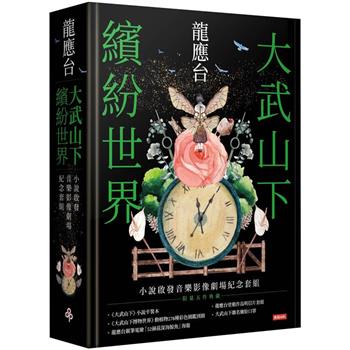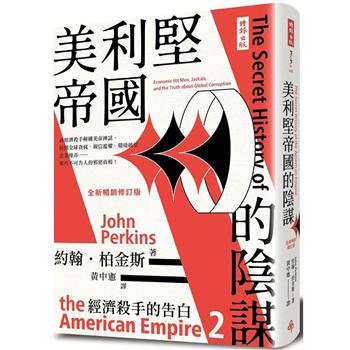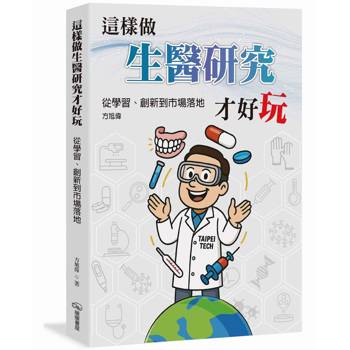Monologue•獨白
……對了,你曾經想過鴿子的事嗎?
我指的當然就是一般的鴿子。在神社裡,或是公園廣場上,咕咕咕地叫著,轉動頭部四處遊盪的那群鴿子。
我常思索這個問題。餐廳菜單上所寫的鴿子,會不會就是平時我們看到的鴿子?事實上,好像不一樣。聚集在神社一帶,頸項有一圈綠色羽毛的這群灰色鴿子,聽說吃起來不太可口。
根據舊約聖經所述,大洪水過後,諾亞看洪水有開始消退的跡象,便將鴿子放向空中。
沒多久,鴿子啣著一片橄欖葉飛回,諾亞因而得知洪水已退。因為這個故事,使得啣著橄欖葉的鴿子至今仍被當作和平的象徵。
如同「鴿子胸(※胸部突出的一種症狀)」這句話所示,鴿子由於有強韌的胸肌以及前端突尖的羽毛,因而具備優異的飛行能力。在無風的情況下,可飛出時速五十到一百公里的速度,條件好的話,甚至能飛上一千多公里遠,完全不用休息。
聽過旅鴿這個名字嗎?一直到十九世紀初,牠都是美國東岸數量最多的鴿子。牠們在美國東部繁殖,範圍從加拿大中南部一直到弗羅里達(Florida),牠們會展開長途遷徙,到美國東南部過冬,因而被人稱作旅鴿。
若不群集行動,便無法繁殖,這是牠們的特殊習性。據說一八一○年在肯塔基(Kentucky)州,有一群左右綿延長達近兩公里寬的鴿群,覆滿天空長達四小時之久,昏天暗地宛如黑夜,推測其數量約有二十二億三千隻之多。
然而,縱使數量多如繁星,但終究還是敵不過人類。人類為了旅鴿的肉和羽毛,需索無度地濫捕,到了二十世紀初,旅鴿就此完全滅絕。
鴿子是採一夫一妻制,終生維持這樣的夫妻關係(這樣確實是能維持和平)。傳信鴿就是因為對伴侶以及鳥巢有這分強烈執著,才會被廣為利用。
早在確立傳信鴿這套系統之前,鴿子便已廣為人們當傳令使用。古埃及的建築物裡,也留有以鴿子當傳令的記錄。船員們即將返抵港口時,會利用鴿子提前數日向陸上的人們通報,而在歐洲希臘,選手為了向家鄉通報自己在奧林匹克競賽中奪得的名次,也都會將鴿子帶在身邊。
鴿子之所以能擔任傳令的工作,全賴牠優異的方向感。經過訓練的鴿子,能持續飛行三百公里以上的距離,也能在夜間飛行。為何牠們能準確無誤地飛回遙遠的巢窩,自古一直是個謎。根據最近的研究證實,鴿子體內含有一種粒子形狀的磁鐵。牠們體內帶著一顆「羅盤」。此外,鴿子的視覺也非常優異,就算離自己的鴿舍再遙遠,也能準確地辨位。
最近看電視時發現,有人竟然訓練鴿子看多幅名畫,然後讓牠從中選出梵谷(Vincent van Gogh)的畫。更驚人的是,將梵谷的畫放在鴿子面前,讓牠看上一段時間後,鴿子不久便記住梵谷繪畫的特徵,能從牠從未見過的圖畫當中,選出梵谷的畫。難以置信對吧?事實上,據說在高科技公司的工廠裡,還利用鴿子來篩選瑕疵品呢。
總之,鴿子除了當咕咕鐘外,還有不少用處。
因此,人們老早便拿牠用在軍事用途上。目的當然是通訊。
起初是在直接以防水墨水在鴿子的羽毛上寫字,不久後,便演變成將通訊文件綁在鴿子腳上,或是將文件放入專為鴿子設計的背包裡。由於鴿子的載重力有限,所以旋即又改成小型底片或小型相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稱此為軍用鴿,每個國家都經常利用鴿子來辦事。美國甚至考慮利用鴿子來誘導飛彈。
但一如各位所知,通訊技術日新月異,人們認為鴿子已被機械超越,失去牠原有的功用。你心裡也這麼想對吧?在這種高科技時代還談鴿子,未免太落伍了吧?
不過,法軍至今仍從事飼育鴿子的工作。在波斯灣戰爭中,美軍為了防範發生通訊斷絕的情形,特地向瑞士軍借來鴿子。瑞士多山,交通不便,自古鴿子便被人們視為重寶。
隨著無線通訊技術的進步,妨礙通訊的技術也同樣日益精進。一旦精密複雜的系統遭到破壞,就只能仰賴物理性的方法。鴿子不受任何雷達影響,也不需要加油,省卻不少麻煩。飛行時會混在其他鳥群中,無從分辨何者是傳信鴿。既經濟,又不用擔心人為破害。在技術發達、戰爭成本激增的現代,鴿子也許將成為日益重要的媒體。
不遠的未來,戰爭會完全採機械化──此事不難想像。士兵們處在四周被電子機器包圍的基地中,探測敵人的位置,遠距離操作發射飛彈。無人偵察機和機器人在地面上四處行動,戰爭處在一種寂靜的狀態。在一片沉默中,只有電腦不斷在運作。無數的電波和訊號在這世界交錯,探尋彼此的所在位置。轉瞬間便可繞行地球數圈的資訊,以億為單位,在宇宙穿梭,其中摻雜著無數假造的資訊。人人疑心疑鬼。戰爭的真正主軸,是分析資訊何者為真。真正的交戰,只要短短數分鐘,勝負立判。大部分的戰爭是與巨大妄想對抗的心理戰。
而真正的資訊,是由鴿子運送。
每個國家都有專用的鴿子,完全透過鴿子進行聯絡。成千上萬的鴿子翱翔在寧靜的藍天之上。無數的鴿子背負著人類手寫的書信展翅飛翔,不必擔心被駭客入侵,或是被竊取解讀。
如何?這幅景象是不是很美呢?
你從剛才就一直露出詫異的表情對吧?不覺得很有意思嗎?
你不懂我這番話的意思?還問我到底想說什麼?
嗯∼簡言之,所謂的價值,具有一種相對性。隨著周遭情況的不同,事物的價值也會隨之改變。只要有一個條件改變,有些事物便會擁有意想不到的價值。
什麼?要我說得更具體一點?
這個嘛。那我說個故事給你聽吧。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發生在短短四天裡的故事……
Fragment1•片段1
前天,我從夏令營返回家中。
久未見面的爸媽前來迎接我時,我看他們兩人的五官是如此平坦,心裡嚇了一跳。也許是因為自己在不知不覺間,習慣了這裡的每一個人以及他們爸媽的長相,才會覺得日本人的爸媽五官是如此平淡無奇。
我很喜歡夏令營。
來這裡之前,我在日本遭遇交通事故,因而住院,就這樣直接來到這裡,沒能和日本的親友道別。來到這裡之後,我有一好陣子拖著傷腿,無法和大家一起玩足球和棒球,一時很擔心自己交不到朋友。不過,因為參加了夏令營,我才能和大家玩在一起,英語也愈說愈流利。這裡的老師和朋友待人和善,都膩稱我「阿和」。
今年的夏令營我玩得很開心。
從夏令營回來後,我日本的表妹跑來找我。明子小我一歲,她笑我的日語怪腔怪調。
我問她到底怪在哪裡,結果她卻咯咯咯地笑個不停,真討厭。為什麼日本人總會笑人說話怪腔怪調?我在參加夏令營的時候,儘管英語說得再爛,也沒人嘲笑我。
不過,日語程度變差,更不是我所樂見。我現在正埋頭苦讀日文書。日後我想從事能來回於兩地之間的工作。
一天之中,我最喜歡清晨。不論是在日本還是這裡,早上都是同樣的聲音。搬運牛奶的聲音。耳聞那卡嚓卡嚓的聲音,感覺一天就此展開,心中無比欣喜。
Fragment2•片段2
(前略)
過去曾談過無數次歷史上的假設。因為我們天真地相信,只要能回到過去,就能改變歷史。以為就像電影膠卷一樣,只要倒帶回去,以剪刀剪下,再接上新的膠卷即可。
然而,我們的認知實在過於天真。我們明白有些事物逝去便無法重拾。這讓我們更加明白,自己對於平日的選擇是如何隨興,何等的漠視自己的人生。
如今,我們得正視現實。這世上並沒有另外一種人生。我們的人生獨一無二,無替代品可以取代。我相信這會提高我們人生的價值,絕不會帶給我們絕望,並希望在此和大家一同確認這點。
不過,我也明白這是非常痛苦的抉擇。對於過去的罪業、過錯、以及無限懊悔、深感唾棄的行為,我們都必須全盤接受。
承認我們過去做過的一切可恥行為,是令人難受的一件事。如今要再度加以仿傚重現,想必有很多人會感受到難以承受的痛苦。但我們必須付諸實行。為了打破這前所未有的困難僵局,我們所有民族都應該睜大雙眼,攜手合作,冷靜行動。
(後略)
摘錄自一九五一年聯合國總會杜魯門總統的演說
Fragment3•片段 3
融化的雪水無比髒污。
周遭又開始恢復帝都熱鬧的喧囂。
隨著交通網絡的恢復,街上登時擠滿人潮,冰雪在人們腳下化為污濁的黑水。
一名穿著學生制服的少年,凍僵的手指交握,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不讓自己滑倒,驀地,他發現灰色雪地中埋著某樣東西。
少年在人群中駐足,緩緩蹲下身,將手伸向那圓形物體。
少年以滿是凍裂的手指將它拾起。卡啦一聲,一條連接在這物體上的鎖鏈碰觸少年的手背,觸感冰冷。
乍看像是黃銅打造,但這滑溜的觸感,卻又顯得有些不同。
它雖然掩埋在雪地裡,但似乎不久前曾被人握在手中,上頭仍留有人的餘溫。
難道是懷錶?
少年朝那銀色的圓形物體不住端詳,不經意地打開蓋子。
但裡頭沒有錶盤,空無一物。只有框邊仍留有些許像是玻璃的碎片,除此之外別無他物。連轉柄也沒附。
可能是壞了,才被人棄置在此。還是說,這是長得像懷錶的另一種東西?
少年側著頭感到納悶,獨自佇立在人潮中,望著手中那空空如也的圓形物體。
FEBRUARY 26, 1936
黑暗中雪花紛飛。
抬頭仰望無數雪花自遙遠的高空飄落,令人憶起故鄉的寒冬。躺在庭園裡厚厚一層雪地上,望著往自己身上落下的白雪,感覺彷如世界就此墜入白色的幽暗中,給人一種不可思議之感。
男子在黑暗中靜靜凝望著雪景。
故鄉的雪,與東京的雪不同。更為天真爛漫,也更為可怕。悄然飄降的白雪,將村莊染成清一色的雪白,逐漸覆蓋在屋梁上。起初還有些含蓄,但不久便慢慢露出它凶暴的面目。大雪連日未歇。就像從浸水的船內往外倒水般,人人身上的衣服滿是斑斑白雪,弓著背不住地剷雪。從一開始降下的白雪變成積雪的那天起,時間過得異常緩慢,人們在大雪底下過著度日如年的生活。
相較之下,東京的降雪顯得有些卑微,而且虎頭蛇尾。落在灰色街道上的雪花,轉眼便已消融,化為污水,沾濕人們的頭髮和皮鞋。這裡飄降的是迷濛雪花,宛如凍結的嘆息。吸入了工廠的黑煙、香菸的煙灰、以及人們的怨懟和牢騷。
但今晚的雪,有家鄉的味道。
也許是斷斷續續連下兩天,在路上積了厚厚一層白雪的緣故,讓他聞到孩提時那熟悉的新雪氣息。
安藤輝三靜靜在雪地上踏步。他伸手探向胸口,悄悄取出小型聯絡器。
打開銀色的蓋子後,浮現淡淡的圓形綠光。看來,目前「確認」正順利地進行著。
螢幕上顯示著一個圓形小時鐘和其下方的方形視窗。上方的小時鐘,是重現的現在時刻。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清晨四點二十一分。
下方則是以數字顯示正式的剩餘時間。
327:50:39
透過被雪沾濕的眼鏡,也可清楚看見上面的數字正逐秒減少中。
這數字證明我目前所看到的事實。在我掌中散發綠光,吸收我體熱的這個機器,是我現在活下去的唯一依靠。但誰能斷言這個數字不是夢?也許我現在人在天國,夢見自己遭槍殺的那一瞬間。
安藤啪的一聲,將蓋子闔上。
他放步朝目的地走去。
沒錯,我應該會遭到槍殺才對。我自殺未成,在接受審訊時,連替自己辯解的機會也沒有,就在刑場地面挖掘的坑洞裡聽見一聲槍響。
但這如此真實的感覺又是什麼?
他豎耳聆聽,身後那無數軍靴像遠方的回聲般,傳來整齊劃一的踏步聲。
那是跟在我身後的第三連隊,有兩百多名士兵。他們是農村裡正値青壯期的重要人手,是奉天皇之名,向他們的父兄借來的重要子弟。
軍靴踩踏雪地的聲響,形成一道波紋,緊跟在我背後。
也許現在跟在我背後的,是昔日由我代為照料的那群年輕士兵的亡靈。他們跟隨著我,對我唯命是從,我指揮這群天皇賜予的士兵,獨斷獨行,他們也許心裡怨恨著我。
當中還有稚氣未脫、雙頰紅通通的新兵。他們今年一月才剛入伍,連軍裝都穿不好。有許多人將年幼的妹妹賣給人肉販子,三餐淨是吃南瓜,導致營養不良,面黃肌瘦。這群青年是如此弱不禁風,就連為他們做體檢的醫師也很擔心,心想──根本就是一群病患嘛。這樣真能悍衛國家嗎?他們吃著軍中的伙食,眼中散發著光輝,彷彿從未吃過如此美味的食物,看著他們,我心中湧起一股無從宣洩的怒意。
這是什麼現實!何等的矛盾!
在安藤的家鄉,聽說村公所還公然買賣年輕女孩。從那些三餐不繼的農村家庭徵調士兵,只會讓這些家庭更加窮困潦倒,但軍中的高層卻在酒樓裡要女人在一旁服侍,汲汲營營於眼前的人事。財政界那批官僚的拜金金義,更是讓人看不慣。他們只會猛撈油水,厚顏無恥地中飽私囊。就算沒有這些問題,在列強的壓迫下,高層也早已後繼無力。軍備縮減的餘波波及士官學校,人們對浪費國家財庫的軍人所做的批評,愈來愈不留情。
新的怒火湧上心頭,感覺兩鬢熱了起來。
沒錯,這條路不管要我走再多次,我也願意。我是出於自願。為了達成昭和維新的目的,我和士兵們一起登上這座斜坡。如果能重新加以實現,我義無反顧。只要能做到,我會放手一試。對自己的這分決心和信念,我無怨無悔。
已逐步靠近目的地。三宅坡前方一片漆黑。
時間是清晨四點五十分。
希望這次什麼事也別發生。
安藤在正式的剩餘時間內第二度襲擊侍衛長鈴木貫太郎的官邸,他全神貫注。
帝都的中樞,正在隆冬的幽暗中沉眠。
然而,在安藤現在行進的三宅坡對面,隔著皇宮,有座巨大的石造建築,裡頭的某個房間有一群忙碌的人們。
這裡是軍人會館。
不過,在此清晨時分,有這麼多人在這裡工作,想必沒人發現。
房內燈光已儘可能降至最暗,窗上還貼有遮光膠膜。
在這約莫二十張榻榻米大的昏暗房間裡,擺著一長排散發昏黃光線的螢幕,一群人守在螢幕前工作。
位於中央的四台螢幕,看起來尤為特別。右邊螢幕一片漆黑,其他三個螢幕則是顯示淡綠色畫面。畫面會不時晃動,改呈黃色,每次顏色改變,便會發出卡嚓卡嚓的刺耳巨響。
一名年約四旬的白人男子守在這些螢幕前,雙眼緊盯呈現黃色的螢幕。
「誤差太大,就快到達極限了。」
一名將紅髮高高盤在頭頂的女子朝螢幕靠近。
「尼克,這是哪一個?」
「第三關鍵點。」
「是誰?」
「栗原中尉。」
「真危險。他沒問題嗎?」
「關鍵點的數量有限制。一次四人已是極限。」
「推薦栗原的人,不正是你嗎?」
「那也是沒辦法的事啊。因為得儘可能挑選有向心力,又是指揮系統核心的人物。」
「已經重來過一次了。一開始就花這麼多時間,還真是沒聽說過呢。連清晨五點的預定襲擊時間都還沒到,就已花了將近八小時之久。」
紅髮女子望著柱子上的時鐘。
顯示現場重現時間的時鐘,與顯示正式剩餘時間的電子時鐘。
電子時鐘上的剩餘時間,正以無情的速度減少中。
327:50:15
「二月二十七日,戒嚴司令部帶了一台竊聽設備來到這裡。一點都不知道我們光是在電話線裡動手腳,就會增加許多不確定因素。」
女子不耐煩的語氣下,流露著不安。
一旁傳來一聲清咳,兩人紛紛轉頭朝聲音的方向望去。
一名身材嬌小的年輕東洋男子,銀框眼鏡底下那對大眼珠,正環視著周遭的成員。
「這起二二六事件,當時本身就有許多謎團。不僅有各種臆測,歷史的評價至今也未有定論。而且人稱黑暗審判的審判記錄也不見公開。要在這起事件中確認真相,可說是困難重重。」
「但聯合國將這起事件視為日本的重要轉捩點。」
「是啊,同時也將此視為介入點。」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如果這麼說的話,不論哪個事件都一樣。我們勢必得從中挑選某個關鍵點,而且既然已經選了,就不能讓先前的準備白費。」
那位名叫尼克的白人男子,雙手在腦後交纏。
「不可能要求完美無缺。但問題是哪裡該妥協,哪裡該讓步。」
身後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尼克心中一驚,鬆開手。
遠處一張旋轉椅發出尖細的嘎吱聲。也難怪會這樣。一名身形奇偉,身體幾欲從椅子上滿出的黑人,雙手抵著扶手,霍然起身。
「現在已無法中止計劃。我們只是要完成任務罷了。『神聖暗殺』當初在執行時,獲得全球一致讚揚,甚至被推崇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功勳。松本,我說的沒錯吧?但誰也沒想到此舉會給美國東部帶來衝擊。再說了,能否確認,並不是由我們來判斷,而是『灰姑娘的鞋』。」
打著紅領帶的男子雙手一攤,指著擺在房內角落的一架大型電腦。
約翰是聯合國的確認指揮官,也是這項計劃的負責人。
「用不著杞人憂天。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紮實地進行每一項確認的事物。
名叫松本的男子微微聳肩,悄聲嘆息,不讓周遭的人們聽見。
一放鬆心情,胃就開始絞痛。他皺起眉頭,緊按著腹部。
沒想到日本是最後一處。而且時間如此緊湊。
他在抽屜裡翻找胃藥。為了不讓自己睡著,就稍微吞幾顆藥吧。
松本喝了一口溫熱的咖啡,連同胃藥一同吞入腹中。
「神聖暗殺」的善後工作費了好大一番工夫,遠超乎想像。聯合國軍在第二次大戰結束時收集了不少情報,所以認為修復相當容易。因此聯合國才遲遲未派員前往日本。記錄確認組織雖主動進行準備,但是要掌握事實的前後關係極為困難。對於聯合國不知變通的介入方式,雖然批評的聲浪不少,但真正的驗證,還是得等到正式剩餘時間結束後才展開。
「約翰,誰持有第四關鍵點?」
紅髮女子不經意地向那名黑人大漢詢問。
男子並未搭理她。
「那是備用的,沒人持有。妳看螢幕,一片漆黑對吧?看也知道。」
「是嗎?我還一直以為有人持有呢。」
女子朝右邊螢幕的漆黑畫面望了一眼。
突然間,從剛才起便一直呈黃色的中央螢幕,卡嚓卡嚓的聲音愈來愈響。顏色也變得益發鮮豔,轉為亮眼的金黃。
「可惡,到達極限,又不行了。」
尼克發出一聲低吼,粗暴地一拳敲向鍵盤。
卡嚓卡嚓卡嚓,螢幕持續發出近乎悲鳴的嘈雜巨響。約翰雙臂盤胸,板著臉緊盯畫面,其他成員也開始內心浮動。
「不行了。得聯絡第三關鍵點。」
女子將手伸向擱在房內中央一張小木桌上的黑色電話。
螢幕畫面驟然轉為鮮紅,中央浮現一排黑字,畫面劇烈閃爍。
不一致。立即中斷重現。
正感覺雪片在昏黃的路燈照耀下熠熠生輝時,驀地銀光驟逝,就像直接被嵌入畫框內一樣,一切靜止不動。
安藤為之一愣。
叮鈴鈴鈴鈴鈴。叮鈴鈴鈴鈴鈴。
傳來一陣鈴響。冰冷、肆無忌憚的鈴響。
二月冷徹的夜空,消融的白雪畫出一道若隱若現的線條,就此靜止。不只是雪。所有存在的萬物──除了他之外──全部靜止。
安藤緩緩轉頭望向身後。
第三連隊在暗夜的雪地中靜止。
無數雪花在空中與這片黑暗緊緊相繫。
跨出的軍靴就此停在半空。
士兵們各以不同的表情凍結。緊張、威嚴、寒冷、不安。微張的嘴唇間,拉出一道唾液的絲線。濕潤的眼球映照遠方的街燈。四列縱隊中間的士兵們抱著一張切成一半的梯子,斜斜浮現在空中。步槍的皮帶在空中彎彎地定住不動。
又中斷了。
安藤定睛觀察過周遭的事物後,這才發現胸前口袋裡的小型聯絡器在震動。聲音震耳欲襲。
安藤取出小型聯絡器,打開蓋子。
螢幕全部閃爍著紅光,上頭浮現一排黑字。
不一致。立即中斷重現。
安藤微微嘆息。
截至目前為止的部分,可以確認嗎?剛才是在重現時間半夜兩點半時中斷。由於朝湯河原而去的河野上尉所租用的轎車,在雪地上打滑,發生擦撞意外。
這次又怎麼了?
些許的疲勞,伴隨深沉的不安湧上心頭。
若是照這個樣子,要重現過去那四天,得花多少倍的時間才能完成?我的體力有辦法支撐嗎?這種事真的能成功嗎?
安藤注視著閃爍的螢幕。
他看到上面浮現數字「3」,看來,離這次出現不一致的場所最近的人,是栗原中尉。
安藤呆立原地。
栗原想必也和我同樣的心思。心裡想著──好不容易上天賜給這樣的機會,竟然無法善加利用,面對這難能可貴的機會,難道不能做些什麼嗎?
安藤在靜止的暗夜中如此反覆尋思。
我能做些什麼?能躲過他們的監視嗎?栗原,你又在想些什麼?
在困難的情況下,要仔細觀察周遭,冷靜判斷戰局。
安藤靜靜沉思。他一面等候那群人的聯絡,一面獨自來回踱步,望著士兵們的臉,在腦海中搜尋因應之道。
應該有什麼辦法才對。他們不知道的事實,只有我們才知道的事實。若能善加利用,儘管只有微乎其微的改變也好,或許能為後人開創一條活路。
在幽暗中,安藤的圓框眼鏡映照出靜止不動的雪花。
叮鈴鈴鈴鈴。叮鈴鈴鈴鈴。
小型聯絡器不斷鳴響。
中斷一切的刺耳聲響。在鈴聲響起的同時,栗原安秀周圍的空氣也隨之靜止。
栗原暗啐一聲,白淨的肌膚因血氣上衝而泛紅,他放下手中的手槍。
他一臉懊惱地從胸前口袋取出小型聯絡器。
打開蓋子後,上頭顯示著「不一致。立即回答。」的文字
只要不回答聯絡器,便無法從這樣的束縛中解脱。
在判定「不一致」的同時,一切重現也隨之停止,之前確認的部分,也會暫時回歸確認前的狀態。倘若一直不回答聯絡器,對這樣的情形置之不理,會加重系統整體的負荷,連之前確認的部分也都將會重新來過。因此,一旦鈴響,出現「不一致」的通知,顯示「立即回答」的文字,無論如何都該立刻按下回答鈕接起電話,這是之前一再叮囑的命令。
已得知「不一致」的原因。
栗原等人雖已出發朝首相官邸而去,但很不走運,路上遇見數名醉漢。看對方三更半夜還在喝酒,似乎令栗原等人頗感不悅。而且這幾名男子個個喝得酩酊大醉,對行進中的栗原一行人糾纏不休。栗原示意下屬不必理會,但年輕士兵對這群不斷糾纏的醉鬼再也按捺不住滿腔怒火(可能也是極度緊張的緣故),最後猛然將對方撞飛。
恰巧位於陡坡,又是冰天雪地,對方因為喝得爛醉,腳下一滑,頭部重重撞向地面。
正當栗原暗叫不妙時,男子頭部呈現怪異的角度,已當場昏厥。
「喂」
栗原按下聯絡器的回答鈕,迅速地應道。
「行動不一致。中斷重現。有人昏倒對吧?是士兵嗎?」
傳來說著日語的女子機械聲。話說相當流暢,但具有外國人特有的腔調。
「是路過的醉漢。緊張的年輕士兵一把將他撞飛。可能把他給撞死了。」
「明白了。重新來過。」
「和你們一開始說的不一樣。根本就完全不同嘛。」
「已加入些許誤差。預定會重回到二十七分鐘前。你在原地稍候。」
二十七分鐘。
栗原微微抬頭仰望。斑斑飛雪滿天,靜止不動。
可以確定這是很吃重的一項工作。
接下來將會一再反覆上演這四天發生的事。不,是在兩個星期內重現這四天發生的一切,真的有可能辦到嗎?
一想到得投入如此龐大的精力,便感到意興闌珊。就算是經過鍛鍊的年輕軍官,這也是相當吃力的體力負擔。
栗原那張像女人般秀氣,又帶點神經質的臉龐,浮現冷酷的神色,陷入沉思。
這根本和我事前聽的完全不同。聽他們說,歷史會主動自行修復。就算我們沒有刻意的作為,昔日發生過的事還是會很自然地重複上演。
栗原收起手槍,靜靜低頭望著自己手掌。
生命線在銀色的皮膚上形成深色的凹痕。就連生命線也一分一秒地在改變。
他以軍靴在腳下的雪地上磨蹭。露出黑色石板。
雖然時間停止,但他身上帶著小型聯絡器,可對雪地施力。此刻的他,可以到任何地方行竊,也能在不被人發現的情況下拿走金銀珠寶。
起初令他大為震驚的眼前光景,如今已開始習慣,栗原對這樣的自己深感不可思議。人就是這麼容易習慣。
話說回來,能接受這樣的情況,更是異常。感覺仍彷如置身夢中。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與嚴謹質樸的安藤相比,身材高佻的栗原,他那清瘦的面容仍留有少年的稚氣。
本以為自己明白他們所做的說明,但經過這數小時後,卻愈來愈不弄不明白。眼前的景象,確實是那天當時的景象沒錯。是昔日親眼目睹過的景象,自己似乎也正重複上演那天發生的事,但剛才的醉漢,以及河野上尉的事故,都是未曾發生過的全新事件。而且一些小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會話中所用的文句,走過的地點。如果這一切都無所謂的話,足見那台巨大的演算機器對於過的去歷史與此刻重現的歷史之一致性,其認定標準相當草率。
栗原是被視為皇道派急先鋒的一名年輕軍官。他個性剛烈,脾氣火爆,但頭腦清晰,能言善道,擁有迷人的魅力。有何思想姑且不論,在邏輯思考方面,他算是相當冷靜。
難道是因為不容許有新登場的人物?
栗原俯看倒在路上的那名中年男子。聽說河野上尉的事故,雙方都掛彩。
他也同樣靜靜地原地踱步,和安藤思索著同樣的問題。
他不明白自己為何置身於這樣的狀況下,但他堅信自己是為了善用某人賜給他的這個機會,才回到這裡。有人在他耳畔低語,要他達成目的。要他完成任務。
栗原微微睜眼,靜靜凝望黑暗深處。
我得保留體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小型聯絡器再度鳴響。打開蓋子後,浮現一排文字。
「重新設定準備完成。正式回溯至二十五分鐘前。請準備。」
栗原回到隊伍前方,重新戴好軍帽。
二十五分鐘是吧。應該會比剛才輕鬆。
毫無預警地,全身猛然感到一陣重荷。栗原不禁發出一聲呻吟。P31黑體?
宛如全身夾滿了衣夾,被吊上空中。
兩鬢、後頸、內臟一陣痙攣。
「噢……」
小型聯絡器的時鐘指針,開始緩緩往回走。
栗原忍受劇烈的重荷,注視著指針。全身仍不住顫抖,冷汗直冒。
指針停止動作,身體登時輕盈不少。
栗原鬆了口氣,望著螢幕上的文字。
「回溯結束。開始重現。」
栗原啪地一聲闔上蓋子,吞了口唾沫,拭去兩鬢的汗水,若無其事地邁步向前。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時間的齒輪上下冊套書(不分售)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440 |
中文書 |
$ 440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時間的齒輪上下冊套書(不分售)
如果能回溯歷史、修復過去……世界一定會更好?!驚人的說故事手法再現,讓你再次迷上恩田陸2008年2月台北國際書展,作者即將來台,敬請期待******************************************************************我們終究還是過於自負。想介入歷史,拯救人類。以為被選中的我們,能將世界導向更好的方向。繼20世紀的黑死病——AIDS後,「HIDS」在未來席捲了全世界人類,造成更大的死亡陰影。HIDS,歷史性免疫缺乏症候群,發生於一群「神聖暗殺者」歸來後數月。他們回到過去,成功抹除人類視為禁忌的記憶和污點,並且安全地回返。這些人是歷史上劃時代的英雄,同時,也是未來致人類於死的起點……★恩田陸?結合歷史與幻想元素,令人眼睛一亮的優秀之作──因發明時光回溯裝置而得以介入過去的聯合國,由於嚴重扭曲歷史,導致人類滅絕的危機。為了避免未來面臨如此悲慘的結果,他們再度修復過去。他們選擇的介入點是1936年2月26日,東京「二二六事件」發生的清晨。與史實有關的三名軍人肩負起這項使命。但三人心中各自有不同的決定。錯綜複雜的時間、空間,以及各自的盤算,交織成難以預料的結果。世界會更好,或是毀滅?當時間的齒輪緩緩轉動,再細微的元素都可能成為關鍵……
章節試閱
Monologue•獨白……對了,你曾經想過鴿子的事嗎?我指的當然就是一般的鴿子。在神社裡,或是公園廣場上,咕咕咕地叫著,轉動頭部四處遊盪的那群鴿子。我常思索這個問題。餐廳菜單上所寫的鴿子,會不會就是平時我們看到的鴿子?事實上,好像不一樣。聚集在神社一帶,頸項有一圈綠色羽毛的這群灰色鴿子,聽說吃起來不太可口。根據舊約聖經所述,大洪水過後,諾亞看洪水有開始消退的跡象,便將鴿子放向空中。沒多久,鴿子啣著一片橄欖葉飛回,諾亞因而得知洪水已退。因為這個故事,使得啣著橄欖葉的鴿子至今仍被當作和平的象徵。如同「鴿子胸...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恩田陸
- 出版社: 奇幻基地 出版日期:2008-01-30 ISBN/ISSN:9789866712098
- 裝訂方式:其他 頁數:608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