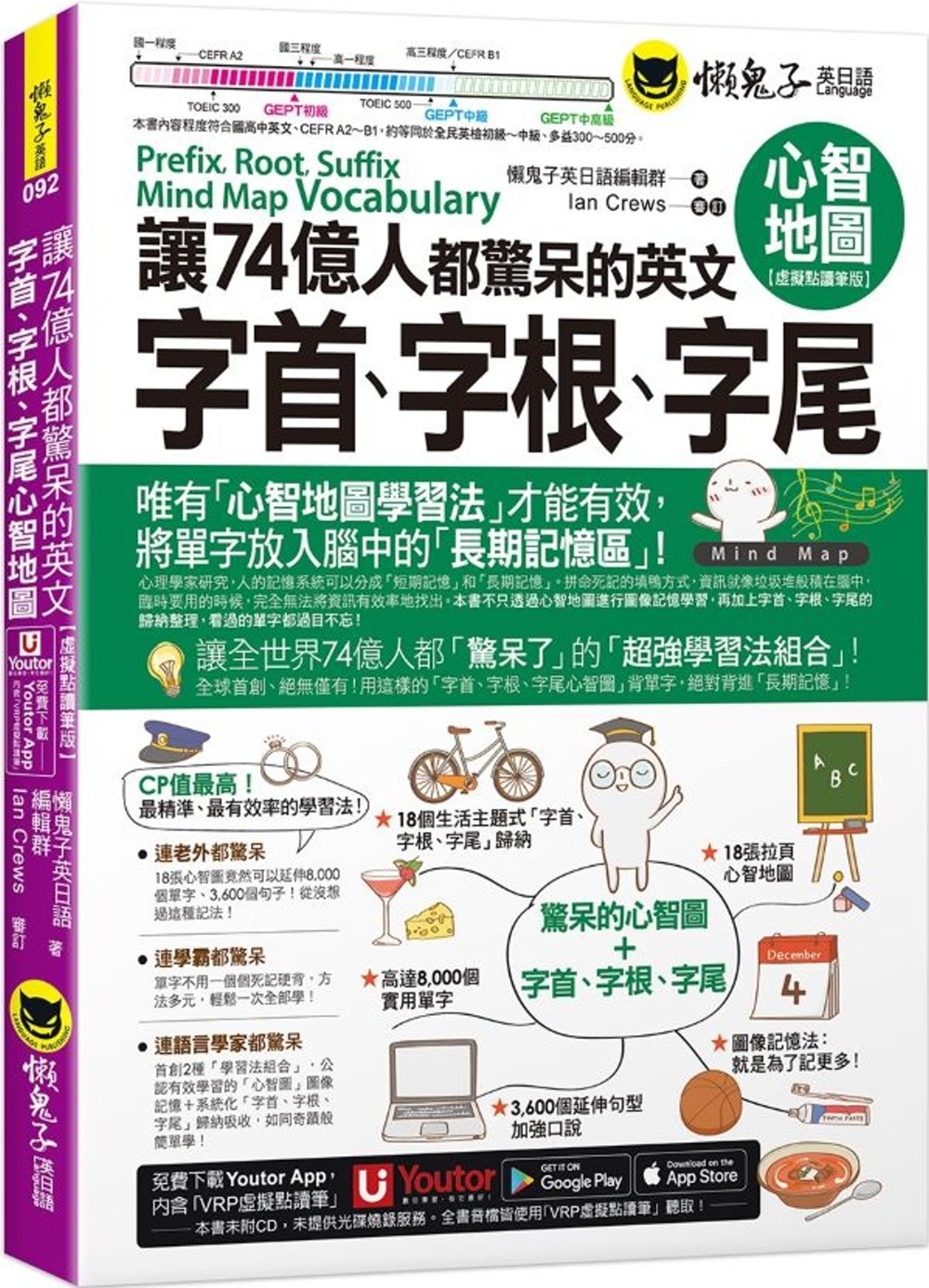音樂思想與理念
郭芝苑一生堅持音樂創作,即使從青年時期開始,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絲毫不為所動。雖然他的家境不錯,但他自幼並無學西樂的基礎。再來,天生的彎曲指頭讓他在學習小提琴、鋼琴上吃足苦頭;接著,父親反對,在日本他曾瞞著父親學音樂,只能省吃儉用從微薄的生活費再省下三分之一,以便支付音樂課別課鐘點費;克服了許多困難,終於考上音樂系,卻是戰事吃緊、連命都幾乎不保,遑論學習?回到故鄉,面臨的是不同的困境,一來無法靠作曲維生賺錢、二來無法進入文藝界主流圈,作品的演出、流傳極盡辛苦,前面多已詳述。許多有音樂才華的人,為了生活,不得不放棄創作,郭芝苑卻能堅持下去,而且不停的學習。
針對作曲理想,郭芝苑說
我的作曲理想是要有民族性、現代性、音樂性(音樂與音響是不同)。就是像古典音樂的傳統技法所發展出來的,能使音樂愛好者感動的作品才好。不是只有少數人欣賞的前衛音樂。德布西、荀白克追求感覺性、理智性的作風還好,但現在有些前衛音樂追求的是音響,非音樂性,甚至變成反音樂,最後連噪音都沒有,只靠視覺的作品也出來了,完全脫離音樂。……我是被西洋傳統音樂所感動而走上作曲這條路,我還是永遠追求能使音樂大眾快樂並感動的現代音樂吧!
這樣的作曲理念,是他一生的信念,一直持續到晚年。雖然大家常說,郭先生蟄居鄉下,不問世事,其實他只是比較木訥寡言,並不退縮。當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數十年封閉自守,世界資訊較難獲得,郭芝苑常請人從日本購買音樂雜誌、樂譜、唱片、書籍等,每天閱讀、進修;只要台北有節目表演,他都儘可能北上觀賞。
「音樂無高低上下之分」是郭芝苑一向的信念,他可以為草民、為歌星寫歌,而不覺得有失身分;他也寫廣告歌曲、兒童歌曲,從不覺得大材小用。早期音樂界不像後來學院派、流行音樂界壁壘分明,他之所以創作流行音樂主要是因為喜歡旋律,他認為流行音樂的旋律最美,寫作流行音樂對他而言是一種休息,可以調劑、舒緩古典創作的嚴肅情緒。儘管有音樂不分高低的觀念,他在很多方面卻很堅持,譬如有人將以往的台語流行歌加以改編,配上管弦樂伴奏,就當成是藝術歌曲;對此,郭芝苑就不以為然的表示,藝術歌曲和民謠、歌謠是不同的,民謠是自古傳來的歌曲,歌謠則是流行歌,將歌謠藝術化就認為是藝術歌曲是很荒繆的。根本之道應是鼓勵現代作曲家多創作台語藝術歌,而不是以非主流來引導主流。
對於藝術音樂,他常說他的創作理念「本土化即國際化」、「民族性即世界性」,認為民族性就是國際性,民族性與國際性是不相衝突的,但這種民族性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解釋。他說:「如蘇聯五人組的作品民族風格很濃,但仍為世人所接受,所謂的世界性就是世人都能欣賞,而且一聽就知道那一國的音樂。而要創作具民族性作品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研究、發掘這塊土地上的東西,像巴爾托克就是以研究匈牙利音樂,創作出自己音樂而為世人所知。」
郭芝苑所持的創作現代民族性音樂的理念,一直持續到晚年。另外,因為社會的逐漸開放、政治漸趨民主化,他心中也慢慢興起以台灣為主體的信念,他的作品從早期就常常以台灣為題,像鋼琴曲《台灣古樂幻想曲》(1956)、管絃樂《台灣旋律二樂章》(1960/1970修訂)、《三首台灣民間音樂》(1973)等,連原來題為「大台北」的進行曲,也修訂為《台灣頌》,1999又完成《台灣吉慶序曲》。
綿延不絕的樂聲
郭芝苑的創作從最通俗的廣告歌、流行歌、民歌編曲、影劇配樂,以及鋼琴獨奏曲、藝術歌曲,到複雜深奧的協奏曲、交響曲、歌劇等,真是無所不包。演唱、演奏他作品的成員,也從毫無音樂背景的婦女團體、販夫走卒、電視歌星、學生合唱團,到國際知名的音樂家、交響樂團。他之所以能如此自在選擇他的工作,如此自由自在的放任自己在音樂創作上悠遊,父祖的庇蔭、留下的龐大家產應是主因──他不必為五斗米折腰,不必為養家糊口而磨滅自己的創造力。
照理說,享有祖先遺產的子弟,生活會比較奢華,郭芝苑卻是一生檢樸。的確,祖先原本留下豐富的田產,可使郭家數代生活無虞,但是經過戰爭,和社會經濟的變遷,尤其是國民政府遷台後施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得郭家祖先所留下來的土地放領了三分之二,家庭經濟頓時受到極大的影響。從曾祖父長年下來孜孜努力的碩果,卻因政府所推行政策,一時之間削去一大半,當年所剩下的產業僅有郭家的投資、山邊的少許貧瘠地,以及他們所居住的大厝。因此,郭芝苑一生緊守著簡樸的生活,可再利用的東西不隨便丟棄,吳玲宜敘述那兩年他一邊寫文稿、一邊寄給她潤飾的情形。她說:「郭先生非常節儉,我收到的手稿,不是寫在稿紙上,而是一張張五顏六色的廣告紙背面。」的確,筆者這十多年來與他通信,也常收到他再次利用的信封;有時他寄來媒體報導的影印給我,直接就在旁邊空白處寫信。
他的個性內向、靦腆、不喜應酬,一生從不管家務事,太太過世後,他甚至不知如何泡茶招待客人。但只要一談起音樂,他即刻兩眼發亮、侃侃而談。他的記憶力驚人,年輕時一些事情的點點滴滴,他都如數家珍,敘述的巨細靡遺﹔他最快樂的事莫過於新作完成、並被好好的演出;相對的,他最憤怒的事情,就是作品被「沒有誠意」的隨便演,他可以因此跟朋友翻臉,也會固執地表示,寧可不演出,也不讓那些「沒誠意」的人蹧蹋。
朋友說他像自天上落入凡間,不知人間事。他常常可以好幾天足不出戶,關在屋子裡讀書、寫作、研究古人名曲,頂多走到院子裡掃掃地,看看心愛的薔薇,或來回踱踱步,在大門內,任喧嘩的人世隔在牆外。偶而外出走在熟悉的苑裡街上,他也很少跟左鄰右舍打招呼,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陷入思考中,不是對人視而不見,就是頭低低地走路。倒是這幾年,他常常早上會到街上走走,或到附近銀行看看報紙,苑裡大街小巷的鄰居都已認得這位台灣國寶。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台灣的真情樂章-郭芝苑的圖書 |
 |
台灣的真情樂章-郭芝苑 作者:顏綠芬 出版社: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3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89 |
二手中文書 |
$ 221 |
音樂 |
$ 238 |
藝術設計 |
$ 246 |
中文書 |
$ 252 |
音樂家/樂團 |
$ 252 |
藝術設計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台灣的真情樂章-郭芝苑
台灣管弦樂大師!郭芝苑是個真性情的文人、藝術家,看似高傲、自負才情,事實上卻非常謙沖低調。他的創作,傳統語法中顯現著現代品味,沒有驚濤駭浪、沒有故弄玄虛,有的幸福洋溢、活潑輕快,彷彿對農村社會真情的回憶;有的恬靜無欲、優雅抒情,彷彿置身於台灣鄉間的世外桃源。其作品除能使知識份子感受其優美和感動,更包含郭芝苑對故鄉的真情。
章節試閱
音樂思想與理念 郭芝苑一生堅持音樂創作,即使從青年時期開始,遭受到一連串的挫折,絲毫不為所動。雖然他的家境不錯,但他自幼並無學西樂的基礎。再來,天生的彎曲指頭讓他在學習小提琴、鋼琴上吃足苦頭;接著,父親反對,在日本他曾瞞著父親學音樂,只能省吃儉用從微薄的生活費再省下三分之一,以便支付音樂課別課鐘點費;克服了許多困難,終於考上音樂系,卻是戰事吃緊、連命都幾乎不保,遑論學習?回到故鄉,面臨的是不同的困境,一來無法靠作曲維生賺錢、二來無法進入文藝界主流圈,作品的演出、流傳極盡辛苦,前面多已詳述。許多...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顏綠芬
- 出版社: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12-31 ISBN/ISSN:97898668334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音樂
台灣的真情樂章-郭芝苑 相關搜尋
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南宋篇):在江南煙雨微茫中若隱若現,越過唐人直奔魏晉的宋人美學I NEED ART:關於我,Henn Kim的成年記述
傳承與開創,從臺灣到亞太—亞洲作曲家聯盟口述史訪談集(國際版)
神聖黑色的魔力:徹底改變人類文明、藝術、歷史的黑色故事
說故事的古典音樂導聆【古典樂派】:鋼琴家帶你入門200首名曲,聽懂巴哈到貝多芬的光明與黑暗
人像繪畫聖經:從不像畫到像,再打破框架!幫你練好基礎、開創風格的人像技法全書 ( 素描 / 插畫 / 電繪全適用)
現代藝術的拓路人:塞尚
韓秀帶你認識西洋藝術家(卡拉瓦喬、埃爾‧格雷考、杜勒、李奧納多‧達‧文西、林布蘭、塞尚)
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宋篇):建立在皇家畫院以外,由士人畫以至於文人畫擔待起來的北宋繪畫藝術
一出手就是名場面:從《樂來越愛你》到《寄生上流》,11大類型片背後的影像拍攝密技&布局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