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真會捉弄人,像這樣的人,居然還有性慾!」
第一本關心身心障礙者性需求的報導文學
性,是生活的根本
性,是確認自己出生意義的一項功課
身心障礙者的性需求該如何處理?
是啊,欠缺某種肢體能力,怎麼能等同於說他/她在性生活上一定困難呢?在性生活上有障礙,但是卻毫不欠缺肢體能力的例子,可是所在多有。
竹田先生受過氣切手術,整天都必須佩帶氧氣瓶,唯獨到色情店的時間完全不用氧氣瓶。療養中心的義工必須冒著極大的風險帶他外出……牛郎店的老闆為殘障者打折優待,他卻不認為是為了殘障者或是為了自己的生意,只是淡然的說:「其實也沒什麼!」「想要支持智障者的性愛權利,並不是閉上眼睛不去想不去看,而是應該想辦法幫助他們跨越危險才對。」事實上,這位社福系教授也積極採取行動,他曾經進入一對智障者夫婦的臥室,輔導他們進行性愛……
這些人從來不標榜「向禁忌挑戰」,只是以最自然的態度面對眼前的身心障礙者,為他們進行「性」的照護。 不論是殘障者或身體健康者,「性」都是生活的根本。但是殘障者的性愛問題和幫助殘障者進行性愛照護的人員,一向被視為不得探討的禁忌問題,本書是第一本探討這個領域的報導文學。
對於完全不了解這個領域的社會大眾而言,作者河合香織用她詳實細膩的筆觸,首先介紹一位片刻無法離開氧氣瓶的殘障者,在照護者的帶領下前往色情店,冒著生命危險取下賴以維生的氧氣瓶,與神女進行性愛,通篇皆讓身為讀者的我們驚訝連連。這位殘障者甚至還說了一句至理名言:「性,就是生活的根本」。
想談戀愛、想做愛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如果無法說出來、如果身體也不聽大腦指揮的話,就很難把性與愛確實加以實踐。例如雙手無法動彈的人,必須央求他人幫忙手淫或是找人做愛。在正常人的世界,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在殘障世界,聽到有專門服務殘障者的色情店,就像是獲得救贖一般令人大感吃驚。作者河合香織實際接觸日本多位殘障者的日常生活及照護義工的工作內容,亦實地走訪對待性愛問題一向先進的荷蘭,採訪了以性愛革命為標的「NVSH」、性愛義工團體「SAR」,讓讀者看到真實存在這個世上、另一個嚴苛的社會。
作者簡介:
河合香織
出生於1974年日本岐阜縣,是報導文學作家。畢業於神戶市外語大學外語學院俄語系,從事社會福利或兒童問題的報導,本書是作者的處女作。
譯者簡介:
郭玉梅
資深專業日文翻譯,從事翻譯工作多年,以文學小說、生活、健康類作品居多,近期作品有《名畫來找碴》、《叫我元氣女王》、《有錢有閒非夢事》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性義工》裡的人,許多並不是「性輔導師」,然而不論是完全做義工的家庭主婦,或專門為身障者所服務的性工作者,都是在為肢體上Disabled的人,提供一種社會的基礎建設,讓他們的生活儘量免於Handicapped……」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
「人間真實有兩種,一種是美好得讓人掉淚;一種是冷酷得讓人掉淚。本書屬於後者。那是正常人所不願面對卻真實存在的難堪。別過頭去,無助於事。坦然面對,翻讀思索,或許,你會從中看到美好得讓人掉淚的人間。」
──文字工作者/傅月庵
「面對性的慾望,那裡一直有一道封印──「不要去揭開它!」大家拼命喊、拼命阻止,以為只要牢牢守住,不要碰觸,就可以化解掉身心障礙者的七情六慾,假裝它們不存在。《性義工》安安靜靜揭開了它。」
──中廣「心靈的春天」節目主持人/丁美倫
「不論這對他們有多困難,窮其一生,他們都未曾放棄,這是多麼令人動容的一刻。」
──樹德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林燕卿
「不再逃避而選擇了面對,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台北縣身心障礙者福利促進協會總幹事/涂心寧
名人推薦:「《性義工》裡的人,許多並不是「性輔導師」,然而不論是完全做義工的家庭主婦,或專門為身障者所服務的性工作者,都是在為肢體上Disabled的人,提供一種社會的基礎建設,讓他們的生活儘量免於Handicapped……」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
「人間真實有兩種,一種是美好得讓人掉淚;一種是冷酷得讓人掉淚。本書屬於後者。那是正常人所不願面對卻真實存在的難堪。別過頭去,無助於事。坦然面對,翻讀思索,或許,你會從中看到美好得讓人掉淚的人間。」
──文字工作者/傅月庵
「面對性的慾望,那裡一直有一道封印──「不要...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拼了命也要做愛——拿掉氧氣瓶的時候
四周漂蕩著消毒水的味道,在這個十個榻榻米大的屋子裡,前面是木質地板,最裡面大約鋪著三個榻榻米,有一個常常在辦公室看到的灰色櫃子,上面放了一個尿瓶。
竹田先生在這裡住了將近三十年,他事先準備了一個字盤(譯者註:字盤是一種可以按下日文字母,一字一字組合成句子的一種表達工具),把他想說的話都打在字盤上。
〈雖然我的手腳不能動 但是只要我還有男人該有的慾望 只要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 做這種事可以讓我紓解壓力 讓我抱持希望活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
竹田先生無法發出聲音。
他曾經接受過三次氣切,喉嚨開了一個洞,由這裡吸入氧氣,而且每隔一個半小時就必須抽痰與更換氧氣瓶,這幾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想說話的時候,也只能聽到噓—噓—的喘氣聲。我曾經數次把臉湊近想聽出他說什麼,卻完全聽不懂。所以,我們後來決定利用輪椅上的字盤來進行對話。但是,他的手完全不聽使喚,一直不停抖動,很難正確指到他想表達的字母,甚至光是把手指指向字盤上的一個字母,就必須耗費數分鐘,所以,要湊成一段文章需要花費更多時間。不過,我還是決定要從竹田先生的一字一句當中,「聽聽」看他的性愛經驗。
竹田先生五十歲的時候,第一次和女性做愛。當時他徘徊在紅燈區的小巷,問過十五家色情店遭拒之後,到了第十六家終於有人肯接納他。根據竹田先生的說法,他不希望自己一輩子都沒有接觸過女性,這樣會讓他含恨而死,所以,才央請療養院的職員帶他逛色情店。
接待他的是一位年約二十四歲的女子,第一次親眼目睹女性身體,竹田先生只能用「美麗」兩個字來形容。但是,對方看到他的身體時,一開始是露出害怕扭曲的神情,緊接著轉變成哀怨的眼神。當時,竹田先生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讓他鑽進去,他後悔得想「拔腿就跑」,但是又怕對不起偷偷帶他出來嘗鮮的工作人員,最後只好讓這件事繼續往下發展──。
「第一次做愛的感覺是什麼?」我問。
字盤上出現他的回答。
「她……肯……讓我……放進去(性器官)……其實是同情……」
就在此時,竹田先生的臉上呈現出扭曲的表情。
他進去的這家店,店名是Fashion Health,本來是以性愛按摩為主,並不提供性交服務。但是,據說這名女子同情他是殘障人士,所以同意讓他把陽具插入她的體內。竹田先生雖然覺得恥辱,卻抗拒不了初次接觸女性身體的誘惑,因為這讓他回憶起年幼時期被母親背在背上的溫馨感覺。
現在,竹田先生從政府補助的殘障津貼當中省吃儉用,每到過年或生日,他就會前往吉原的Soapland,讓自己「快樂」一下。
對於整天二十四小時都必須隨侍在側的兩支氧氣瓶,竹田先生也決定在這寶貴的時間當中,暫時取下它們。因為在兩小時的「做愛期間」,這兩支氧氣瓶實在礙手礙腳。
「呼吸……很痛……苦……但是……像孩子一樣……搓弄大奶……很爽……」
「這樣可能會死掉的!」我說。
「那就算了……做愛……才是最重要的……不能……丟掉……生活的根本……」
即使是上色情店,竹田先生也無法獨自成行,有幾位免費義工願意幫忙帶他前去。佐藤英男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竹田先生居住的殘障療養院的社工人員,今年四十五歲,擁有一個和藹可親的圓鼻頭。
帶竹田先生外出需要冒很大的風險,但是,佐藤先生卻深深不以為然。
「萬一發生什麼意外,當然必須由我負全責,但是,為什麼我還願意這麼做呢?因為這件事讓我感到快樂。這些對自己毫無自信的殘障者,在走出那道門之後,個個都顯得神采飛揚,光是看到他們的表情,就讓我非常感動。」佐藤說。
他不僅要幫助殘障者在色情店移動身子,還必須幫他們脫衣、洗澡,在殘障者「做愛」的期間,他就在會客室等待,等到完事之後,才把殘障者帶回去。由於每一個「做愛的動作」都相當耗費時間,所以,通常必須花費較高的費用。
有時候,佐藤先生甚至必須充當殘障者的「手」,幫助他們手淫。
「這種事只能做不能說。當我幫助殘障者手淫時,有時候現場也會有其他人,所以,其實也沒什麼。」
我一直認為,男人幫助男人手淫,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但是,佐藤先生似乎並不這麼認為。
「其實這根本不算什麼,可以說是小事一樁。」佐藤說。
或許是因為佐藤先生對這種事抱持自然的態度吧!許多殘障者遇到開不了口的性愛問題時,他們都會找佐藤諮商。
不過竹田先生願意讓佐藤帶他到色情店,卻不會開口請佐藤幫他手淫。這是為什麼呢?
竹田先生曾經在錄影帶中說過一句話:
「接受他人的看護與協助,對我來說是最大的屈辱,不過,我會忍耐,因為那是為了活下去……」
五十歲以前從未有過性經驗的竹田先生,為什麼會下定決心到色情店「嫖妓」呢?
「因為……我的……女朋……友……去世……了。」
他用顫抖的手指按下一個又一個字母。
「死……死於……意外……」
「你們交往幾年?」我問。
「十………」
竹田先生用他全身的力量,按下一個又一個字母。
「十………五………年」。
「十五年!」我露出驚訝的表情。
看到我吃驚的神色,竹田先生用拇指和食指比出OK的手勢,臉上露出難得一見的笑容。
竹田先生一生唯一的戀人,名叫山岡綠。竹田三十幾歲住進醫院時,山岡綠當時是護士。
他們兩人是在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相遇。當時,竹田先生一再違反療養院規定的禁酒令,因為屢勸不聽,院方決定把他送到精神療養院。根據竹田生先的說法,當時人們對殘障者大都抱持歧視的態度,甚至以「廢人」這種鄙視的字眼來稱呼殘障人士。
當時有一位名叫「水上勉」的知名作家,他的兒子一出生就是重度殘障,因此,很沉痛的向社會大眾發表他的觀點。
「如果整個社會不改變對殘障者的看法的話,倒不如在重度殘障者一出生的時候,就立刻給與安樂死!」
當時,整個社會正陷入安樂死是否合理合法的探討熱潮當中,多數殘障者對於安樂死都極為反感,但是,竹田先生倒沒有堅決反對,因為每當他想到自己的未來時,真恨不得能夠一死百了。
他所住的病房大約五十個榻榻米大,住了三十個人,房間裡沒有任何隔間,竹田先生認為這根本稱不上是「房間」,應該說是「人肉倉庫」。
就在他灰心喪志的那段時期,他發現有一位護士每次走過房外的走廊時,都會哼著當時非常著名的流行歌曲「赤坂夜深」,雖然有點荒腔走板,卻聽得出歌聲裡帶著愉悅的心情。
「為什麼這個時候還在這裡呢?
搖晃的燈影陪伴割捨不了的想念,
明知自己深愛著你,
卻只能輕輕呼喚你的名字,
想要見你的念頭一直揮之不去,
赤坂的夜,更深了!」 (作詞、作曲:鈴木道明 歌唱:西田佐知子)
山岡綠當年二十八歲。
根據竹田先生的說法,山岡綠的身材健美,有一張方臉。
她的外表看似剽悍,卻有一顆溫柔的心,而且行事穩重,感情內斂。
山岡小姐每天必須背著五十公斤的竹田先生,經過大約三十公尺的走廊到達浴室;有時候會用碎布為竹田先生縫製坐墊,甚至還會為他沖泡當時才剛上市的即溶咖啡。總之,在不知不覺當中,愛苗已在他們兩人的心中慢慢滋長。
但是,就在他們認識五十天左右,有一天,山岡小姐突然辭職離開醫院,這件事令竹田先生難以承受。經過一年八個月之後,竹田先生終於探聽到,山岡小姐是因為罹患重病,被送到別的醫院治療。於是,他們兩人終於又有機會再度見面。
竹田曾經為此事吟詠了一首詩:
不知何時再見 不知如何相見 我日日夜夜心急如火
自此以後,他們大概每隔一個月就會見面一次,有時是竹田先生到山岡住院的地方探視,有時是山岡前往竹田居住的療養院,這種約會型態就這樣維持了十幾年左右。
每次山岡小姐前來竹田先生的住處時,一定會用臉盆裝上熱水,溫柔的擦拭竹田先生的臉和手,並且耐心的為竹田先生修剪指甲。當山岡小姐很想要一個錄放音機的時候,竹田先生就會利用年終大拍賣,以半價的金額買下來送給她。
我實在按耐不住,很失禮的問他:
「你和山岡小姐上過床嗎?」
「嘴……和嘴……」
「你的意思是接吻?」
竹田用手指比出OK的手勢。
這件令人難忘的事情就發生在一九七九年(昭和五十四年)九月,竹田先生一如往常前往山岡小姐住院的地方探望她。他們兩個人一起到距離醫院約二十分鐘路程的超級市場購買食品,包括有咖啡、仙貝、餅乾、泡麵等等,就在回程中,山岡小姐突然停止推動輪椅,並順勢把嘴唇壓向竹田先生的嘴唇。
「抱歉,我從沒做過這種事,所以技術還不太好……」山岡說。
路人以訝異的眼神看著這一幕,但是,山岡小姐卻絲毫不在意。
「為什麼那些人要這樣看我們呢?管他們的,反正我喜歡這樣。」
但是,五個月後,山岡小姐卻臥軌自殺,結束掉四十三年的短暫生涯。她是因為罹患重度精神衰弱,讓她對人生感到失望。就在山岡小姐死亡的九天後,竹田先生前往醫院探望她的時候,才從醫院職員口中得知這項消息。
交往了十五年,總該做過愛吧!
「沒……有……」他從身體的最深處發出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喜歡……她……」
「喜歡她?那就更應該想和她做愛呀!」
竹田先生很努力想說些什麼,卻發不出聲音,他把視線移往字盤,開始組織他所要表達的意思。
「其實……我……」
竹田先生突然把手移開,就此停住。
休息一段時間之後,又有字母浮現出來。
「我也……很想……做……但……我這種……身體……造成……她的……負擔……」
在十五年的交往期間,竹田先生甚至從未說出「喜歡妳」三個字,每次見面,總是一再叮嚀她趕快找個好人家嫁出去。因為竹田先生早已下定決心,為了她一生的幸福,儘管自己非常喜歡她,也絕對不說出口,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愛情。
山岡小姐去世兩年後,為了排遣寂寞,竹田先生才主動拜託療養院的職員,帶他去色情店。因為唯有在進行性行為當中,他才能完全遺忘山岡小姐,但是,一回到療養院,山岡小姐的身影又立刻浮現在腦海裡。
就這樣經過了近二十年,竹田先生前往色情店的次數多達數十次,儘管事後對這種金錢買賣的性事讓他感到後悔,但是他認為接觸年輕女性的肉體,讓他感到非常愉悅,更讓自己變成有自信的男人。過去,他曾經因為自己的身體殘障,也為了愛人先他而去,數度萌生自殺的念頭;但是現在,他卻希望自己能夠長命百歲。
「但……是……」除了用手指按下字母,竹田先生還拼命發出沙啞的聲音,他瞇起雙眼,緩緩閉上眼睛。
「真希望……能夠……和她做愛……即使……只有一次……」
在色情店「辦事」的時候,竹田先生常常把山岡小姐的影像重疊在性工作者的身上,儘管山岡小姐已經逝世二十多年,仍可以感受到他對她的歉疚感。
「我很想……和女人……交往……也……很想……結婚……也想……有小……孩……也想……讀書……但……一點……資格……也沒……有……」
突然,一滴滴的淚水緩緩滴到字盤上。
丁美倫:我和我的殘障朋友們的愛慾情仇
那件事發生的時候,我才讀完《性義工》譯稿沒多久。
在殘障協會的活動上,我發現一個六十多歲的阿伯緊盯著我,後來我上洗手間,他也跟過來了。
「我有話對妳說」。「說ㄚ」。「我真的要說了--」。「你就說ㄚ」。
那是我們在廁所前的對話。
他終於說了,帶著羞愧的神情:「嗯,剛剛看見妳,我---射精了,因為我受過傷,腦子雖有那種想法,卻不能和身體連接起來,剛才卻---。嗯,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我很想告訴妳這件事。」
然後他的臉上浮現一種「我總算還可以」的快慰。
不知為何,面對那樣的場景,一個身障老人誠實的告訴我他射精了,而我並不覺得猥褻,可能是因為剛剛讀完《性義工》的關係,一本日本女作家探討身障者性需求的報導文學。
面對性的慾望,那裡一直有一道封印,「不要去揭開它」大家拼命喊,拼命阻止,以為只要牢牢守住,不要碰觸,就可以化解掉身障者的七情六慾,假裝它們不存在。
《性義工》安安靜靜揭開了它。
而對自己成為身障者的性幻想對象,我有一種比「深感榮幸」更複雜、更迷惘的心情。
然後我想起了一件更早以前的事。
我們殘障協會辦公室一直由一群智障生負責打掃,其中有個男生似乎很喜歡我,每次看到我都會靠過來,碰一碰我,喊姊姊、姊姊,那天也一樣,他喊了我「姊姊」後,才一轉眼,因為剛好穿著一條黑色褲子,很明顯我看出他射精了。
「不好意思,妹妹」輔導老師也知道發生了什麼,過來拍拍我,怕我被嚇到「他雖然只有八歲的心智,但身體卻是三十五歲的身體」
一個三十五歲的男人,看見了喜歡的女人,勃起、射精,這在正常人的正常世界中再正常不過,但發生在一名35歲的智障男人身上,它就成了一個不可說、不能說、不知該如何說的禁忌。
「那你們都怎麼輔導?」我問老師。
老師告訴我,有些智障者家庭會帶小孩去結紮,而社工員能夠做的,也就是轉移、轉移、轉移。轉移才能昇華。
但我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為了傳宗接代,在看不見的角落,不知有多少父母為他們的智障兒「買」一個外籍新娘,而我所認識的一名智障女,我不時看到她大腹便便的樣子,所以便有一種惡意的說法不斷在傳播,說是一旦體會過性愛的滋味,身體被喚醒了,這樣的女人便會再度渴望,男人便有了趁機而入的機會,畢竟性是本能,而且永遠不能滿足。
到底智障者有沒有性的自主權?該不該生育?結紮人不人道?「智障者不是中性人」,身心障礙服務資訊網上有一篇「唐氏孩子的性教育」,文中提及美國學者Gordon的主張: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要求適當的教育,智障孩子也和所有人一樣,需要愛和被愛,需要肯定其價值,並接受其為性的個體,「在近乎完全壓抑與否認性慾的情況下,成熟的智障兒在這充滿刺激的現代社會中,愈迷惑與不安」他說。
這讓我不斷想起《性義工》中,那些幫助癱瘓者自慰,或者帶他們到色情店「開查某」的日本社工,還有荷蘭,它竟然存在一個為身障者提供性服務的團體SAR。
那是怎樣一個人權至上,觀念高度進化的社會,像遙不可及的天堂,不然怎會在維繫身障者的生存之外,也照顧他們的心靈,正視性的需求。心靈和性,某些情況下它們的意義是相通的。
*我
我,43歲,八個月大的時候,罹患了小兒麻痺症。
我可以說是在男人堆中混大的,與我的父親、我的三個哥哥(加上哥哥的朋友),還有幾十個舅舅,我一出生就面對一卡車的男人,男人這種動物對我來說等於天生自然的存在,而我則是父親最渴望得到的女兒,倍受寵愛。
因為和「正常男人」太熟了,我幾次的戀愛對象都是和「正常男人」談的,也沒有殘障的男孩正式追過我---事實上有過,但他表達愛情的方式太不明確了,我是那種你如果不直接明白告訴我「我喜歡你,我在追你」,便不知對方意圖的女生,無論再怎樣暗示,怎樣默默守候都沒有用。
等到他明白告訴我時,是在我結婚前夕。
但即使我得到那麼多的親情和友情,殘障的程度也不嚴重,被歸類為「殘障圈中的幸運兒」,二十歲以前,走在路上我時時刻刻都在注意別人的眼光,覺得每一個人都在看我的腳,我身體最醜陋的部分。
二十歲是一個分水嶺。
那一年我準備去自殺,因為自覺沒辦法走出殘障的陰影,不想活下去,於是在租屋處寫好了遺書,向房東說再見,便出發去烏來。我沒去過烏來,但書上說烏來再進去有個山明水秀的福山,我想到一個陌生而美麗的地方結束生命。
那天不是假日,通往福山的客運車上空空蕩蕩,但有個男孩卻走過來問:「我可以坐妳旁邊嗎?」,我無所謂的點點頭,他就坐下來了。
當時我萬念俱灰,心想自己臉上應該是一片平靜,不然就是一副就要慷慨就義的從容神色,但他似乎覺察了什麼,坐下後忽然開口問道:「妳怎麼了?妳要去做什麼?」
「我有怎麼樣嗎?」我回問他。
「反正我們素昧平生,下車以後可能再也不會見到,所以心裡有什麼事,可以告訴我」他繼續說。
我想他說的沒錯,我們很容易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剖心掏腹,說出秘密,因為我們不會再相見,所以我決定告訴他,我要去自殺。
「妳長這麼美,死掉太可惜了」。「你沒看到我的腳嗎?」。「那又怎樣?」。---
我們就這樣一路聊下去,我知道他在台大心理研究所念書,他要在我前面一站下車,下車前他給了我一個名字和一個電話,「如果你沒死,一定要打電話給我;如果死了,我也祝福你,自殺成功。」
到了福山,冷風颼颼,我的心開始動搖了:「我要死嗎?」、「我真的那麼想死嗎?」、「我非死不可嗎?」
一念之間,我忽然覺得自己應該要回家。
我回來了,卻忘了那個人和那隻電話,五年後,我準備要搬家,從一本書中掉出一張紙片,上面是他的名字和電話,覺得欠他一個謝謝,便撥了號碼,沒人接,再撥,也沒人接,最後再打一次,快午夜十二點了,有人接起電話便說:「妳是丁美倫嗎?我等這電話等五年了」
他說他只把這電話給了一個人,我,這五年間他出國念書,在國外工作,剛好回來台灣,一直沒換電話,就覺得我一定會打電話給他。
他成了我的男朋友,我們交往了幾年,其間還有人用「那個小兒麻痹的女人不配和你在一起」這種理由來橫刀奪愛,後來他在美國發生重大車禍,兩位同車朋友當場死亡,他沒有外傷,車禍後還急忙託人打電話找到我,確定與我聯絡上之後,眼睛一閉便走了。
有人說男人對拄著拐仗的女生有一種特別的好奇,甚至會想像進入她們身體的感覺。
所以我因此差一點被計程車司機強暴,當時夜色已深,我被他載到河堤,我想他是要在車內強暴我,拉拉扯扯之間,他碰到了我的支架。「這可以脫嗎?」他問。
「不可以」我大聲尖叫。
我猜他或許感覺像碰到了機器人,冰冰冷冷,忽然生氣的喊:「妳下車」。
我倉徨下車,剛好碰到一個守望相助巡邏員,重返人間。
經過不斷的治療,現在的我只用一副支架,當時我的狀況很嚴重,必須穿兩副到腰桿的支架。
後來我開始工作,職場上總是不斷有男同事問我:妳的支架可以脫嗎?妳的支架可以脫嗎?
據說正常男人對殘障女生懷有強大的同情心。同情、好奇與愛情,糾纏不清。
*她們
是她第一個把「性」放在我的意識裡。
她是我朋友,大我一歲,和我一樣得了小兒麻痺,有一次我到她家,看見她書桌前貼了一張表,上面寫一串男人的名字,後面則標記各種不同的顏色,藍的綠的紅的---。
「這什麼意思呢?」我忍不住好奇問。
「上過床的就畫紅色,擁抱過的藍色,親吻過的紅---」她回答起來一派自然。
「妳這是---」我腦中想到的是「賣身」兩個字。
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繼續解釋:「我們殘障女孩子也是女人,何況我也長得不錯,為什麼不能去追求想要的?」
那時我還很年輕,二十出頭,閉塞的很,而且以為不會有男人會想要和殘障的女孩子做愛。
她卻告訴我完全相反的事:很多男人,正常的男人噢,反而對我們這樣的女孩子充滿了憐惜、同情,還有好奇。
那是我第一次接受關於性的震撼教育,但在一個男人面前把支架脫掉,我覺得我還是做不到,至少還沒有遇到這樣一個能夠讓我拋開障礙的男人。
後來我的閱歷不斷增加,談了戀愛,結識更多男女朋友,加上工作關係深度採訪過各種障別的人,我發覺她的說法有幾分真確。
身障者因為渴望與壓抑,性的想像有時反而更強烈,用想像點燃慾望,這想像和慾望或者會轉移到工作,到創作,也可能召喚出超乎正常的性需求,以證明自己的存在。
在情趣玩具網站上,我知道很多購買者都是殘障朋友,有一天我的一個殘障女朋友就向我展示她郵購的電動陰莖,「拜託,自己解決就好了,我們何必為了喝牛奶去養一隻牛?」
殘障者和非殘障者之間,似乎沒有太多的不同。
*
二十九歲,我終於遇到了一個讓我自然而然脫下支架的男人,我結婚了,現在有兩個女兒。
他從來沒有把我當成殘障人士看待,這是我婚前所期望的,卻也是我婚姻衝突的導火線。除了煮飯(謝天謝地他肯煮飯),所有的家事全部由我包辦,有一次我把健康的腳跌斷了,打上石膏,但我這人有潔癖,受不了地板髒,只好奮力用石膏腳爬來爬去拖地,而他好端端的坐在沙發上說「這地板不髒ㄚ」,完全沒有幫忙的意思。
生二女兒時,她哭鬧不停,我吃力的抱起她哄騙,你知道殘障者抱小孩有多困難嗎?但做爸爸的只會嫌吵,一點也沒有接手的意思。
到底我能做多少,他又該做多少呢?這尋常夫妻之間的爭執,似乎更嚴酷的考驗殘障者的婚姻。往好的一面想,他根本把我當正常人看,所以在他面前脫掉支架就成了一件自然的事,除了他,我想我在其他人面前都做不到。
*不可思議的愛與恨
我不太相信自信可以克服一切,但沒有了自信和正面的力量,每一個人都是程度不等的殘障,而殘障的她就是憑著不可思議的自信,建立了一個家。
她是一位口足畫家的妻子,全身上下只有三根手指頭是靈活的,非常嚴重的殘障。他們相識相愛,決定結婚時,口足畫家的老父親大力反對:「我兒子已經沒有手了,妳癱在輪椅上,你們怎麼可能結婚?」
「你兒子沒手,我有三根手指頭」她這麼對老人家說。
事實證明她沒有錯,她不但生了小孩,自己照顧小孩,還能煮飯、做代工,一直到丈夫收入慢慢好轉。
但那畫面說來辛酸,他們住在小閣樓,每天要上樓睡覺前,丈夫得把妻子綁在身上,慢慢爬上去,接著再下來把女兒用嘴巴叼上去。兩人騎摩拖車時,也必須把她綁在車上,否則她會掉下去。
「妳們怎麼生小孩?」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問她。
「妳又怎麼做?」她這樣反問我。
我仍舊猜不出來他們如何辦事,只確定她是一個心裡有太陽的,非常勇敢的女人。
男人呢?同樣脊椎損傷,全身癱瘓的男人,他們的另一半很多都是協會專業社工員,這樣的例子我至少知道五對。
「他全身都不能動,怎麼做?」我問過他們的妻子之一。
「妳以為做愛是全部嗎?」那位妻子反問。
「當然不是全部,但我好奇」我再問。
「他們不是不能做,受到刺激的話,還是可以勃起,只是他們不知道,沒有感覺」妻子進一步解釋。
身體需要養分,就算不感覺到餓,還是要吃東西,我想沒有感覺的性大約就是這樣,做愛不單只是為了獲得快感,它還有具有更深層的意義。
就有一個罹患脊椎癌的妻子,她的脊椎佈滿了癌細胞,連上廁所都得一直拍打才能排尿,做愛當然不可能有感覺,可是為了丈夫,她已經練就到靠著注視丈夫表情的變化就可以發出配合的嗯啊聲,他知道她沒有感覺,她知道他想要做愛,因為愛,她甘心情願。
也有人一直活在陰鬱中,慢慢枯萎。
她是一個比我美麗一百倍的女孩,大我一歲,殘障很嚴重,卻不肯穿支架,又不知為何老愛穿短裙或短褲,露出兩隻萎瘦得比鳥仔腳還細的腿。當她撐著兩根柺仗一步一步邁進,每跨出一步都讓人擔心下一步就要撲倒,看見這樣的畫面,沒有一個男孩能不對她伸出手。
在外面,大家都說她的個性像天使,沒有人不喜歡她。
但我和她越熟,越是看到另外一個不同的她。在家裡的她完全像另一個人,是頤指氣使的女皇、女暴君,水果明明擺她面前,她會指使說「哥,切一塊給我」,也經常在浴室大呼小叫:「媽,把我的洗髮精拿來」,總而言之全家人都得小心翼翼侍候她。
我十三歲就離家,個性獨立,少有事情是我覺得自己做不來,需要別人幫忙的,就算做不來我也會勉強去做,這使我很難忍受她的任性和囂張。
「對不起,我不和你做朋友了,就算身體有病,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家人?」
「好,丁美倫,妳要知道嗎?」
她把我帶到房間,脫掉衣服,露出一條像蜈蚣一樣的手術疤痕,她的脊椎開過刀,整個脊椎呈S型側彎。
「我沒有辦法走出自己,丁丁,妳怎麼能體會我呢?妳很幸運,長得不錯,只是腳有點變形,男孩子也願意正常和妳交往,對我只有同情、可憐,沒有人要和我交往,抱我,我更沒有勇氣在男人面前脫掉衣服--」
我看著她扭曲的背脊,心想如果我是她,我會和她一樣把對命運的憤怒丟給家人嗎?我會活得比她更好嗎?
我不知道。
我們不再往來,是因為我要結婚,而她始終不肯相信,無法接受這件事。
我知道她真正渴望的是做愛,她想要做愛,就算只有一次也好。
還有更悲傷的故事。因為家裡開貿易公司,她就在自家做會計,從小家裡只要有客人來,或者後來哥哥結婚,就會聽到有人大呼小叫:「妳快去躲起來」,擺明家裡有一個這樣的孩子是見不得人的事。
「妳結婚了,好羨慕妳」有一天她對我說。
姑且不論我的婚姻好不好,因為我結婚了,而且和一個正常的男人結婚,光是這件事就讓我殘障圈的朋友們羨慕不已。
後來她家的公司收了,但她手邊還有一點錢足以養老,便和一個大她十多歲的計程車司機在一起,之後那男人連車都不開了,住她的吃她的喝她的。
「妳何必呢?」我們經常苦苦勸她。
「妳不知道,他對我很好,從來沒有男人願意親我、抱我」她甘之如飴。
後來實在撐不下去了,她只好出去打零工,每個月賺一萬多,男人只負責接送,還是不肯開計程車。
沒有人不渴望被擁抱,被愛撫。殘障圈中,不知有多少女人為了愛,或說為了性,被騙到一身精光,下場淒涼,但終其一生沒有交過男朋友的人更多,「不可能的事」,她們一開始就不抱希望,封閉自己,拒絕受傷,像二十歲以前的我。
*幸福的婚姻?
殘障的女人經常受別有居心的男人騙,那麼殘障男人是不是比較容易博得女人的同情,以及愛?
我訪問過幾位事業有成的殘障人士,他們都娶了正常的妻子,表縣上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但真的幸福美滿嗎?答案和正常人的婚姻一樣,十對中恐怕只有一對真正的幸福美滿,另有一半以上,幸福美滿來自丈夫的百般忍耐。
有一位十年前年薪便破三百萬元的證券營業員告訴了我他婚姻的真相—他的殘障十分嚴重,放掉拐仗一步也不能行,當時是妻子主動追求他,他們婚後搬進了豪宅,主臥室便有十幾二十坪大,每當妻子把地板拖乾淨,便不准丈夫拄著拐仗或推輪椅進來,怕留下痕跡,所以他必須用爬的。半夜若小孩哭,起來沖牛奶的人也是他,因為要用兩手推輪椅,所以只能把奶瓶夾在兩腿間,以致大腿被常燙傷。
「為什麼不離婚?」我問他。
「大家都說我們是一對恩愛夫妻,妻子多麼照顧我---」他給了我一個不像回答的回答。
妻子還常以不做愛來威脅他。
我可以猜想,在年復一年的婚姻生活之後,妻子必然會開始抱怨丈夫的性能力不夠強,不夠持久,不夠狂野,而她則配合、將就的太多也太累,已經不想再繼續了。
不對等的性,不對等的關係,婚姻就失去了平衡。
最後他們還是離婚了。
性是婚姻的重要元素,卻也可以如浮雲輕煙,我不知天底下有多少無性但和樂的夫妻,但我認識一對真正的無性夫妻,他們兩人都是殘障者,生活在一起,相互扶助,也都寄情於宗教。
當性消失,愛的感覺還是可以延續吧。
*
《性義工》呈現了一個距離台灣社會非常遙遠的世界,一個讓人落淚的異境,它觸動我的回憶,也讓我想起太多發生在身邊的故事,關於我和我的殘障朋友們,而我說出來的不過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
太多的主張都說,性,那是一個不能碰觸的問題,不能揭開的封印,殘障者只要能夠生存,只要活著就是上天的恩寵了。
現在我們卻知道事情不一定是這樣,很多故事沒有被說出來,被遮蓋了,我們有權利作為性的個體。
但我想問的是,假設性的需求被喚醒,面對各種障別的人,我們的社會能夠做什麼呢?如何理解和對待?會有人願意成為性愛義工嗎?
我們的社會顯然沒有準備好,《性義工》不過是一個微小的呼喊,祈求社會的回應,這就足夠了。
第一章 拼了命也要做愛——拿掉氧氣瓶的時候 四周漂蕩著消毒水的味道,在這個十個榻榻米大的屋子裡,前面是木質地板,最裡面大約鋪著三個榻榻米,有一個常常在辦公室看到的灰色櫃子,上面放了一個尿瓶。竹田先生在這裡住了將近三十年,他事先準備了一個字盤(譯者註:字盤是一種可以按下日文字母,一字一字組合成句子的一種表達工具),把他想說的話都打在字盤上。 〈雖然我的手腳不能動 但是只要我還有男人該有的慾望 只要在經濟許可的範圍內 做這種事可以讓我紓解壓力 讓我抱持希望活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 竹田...
目錄
推薦文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
樹德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林燕卿
台北縣身心障礙者福利促進協會總幹事/涂心寧
序章 畫面的另一邊
第一章 拼了命也要做愛
拿掉氧氣瓶的時候
第二章 十五分鐘的情人
徵求「性愛看護」
第三章 殘障者專用的色情店
失聰大學女生的選擇
第四章 白馬王子是牛郎
女性殘障者的性愛
第五章 是誰在睡覺?
智障者的環境
第六章 響個不停的電話
荷蘭「SAR」的現況
第七章 永不停歇的思念
市政府的性愛協助
第八章 性伴侶的夢想
目標就在前方
最後一章 偏見與美談之間
後序
文庫版後序
解說─高山文彥
後記─丁美倫:我和我的殘障朋友們的愛慾情仇
參考文獻
推薦文
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
樹德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所長/林燕卿
台北縣身心障礙者福利促進協會總幹事/涂心寧
序章 畫面的另一邊
第一章 拼了命也要做愛
拿掉氧氣瓶的時候
第二章 十五分鐘的情人
徵求「性愛看護」
第三章 殘障者專用的色情店
失聰大學女生的選擇
第四章 白馬王子是牛郎
女性殘障者的性愛
第五章 是誰在睡覺?
智障者的環境
第六章 響個不停的電話
荷蘭「SAR」的現況
第七章 永不停歇的思念
市政府的性愛協助
第八章 性伴侶的夢想
目標就在前方
最後一章 偏見與美談之間
後序
文庫版後序
解說─高山文彥
後記─丁美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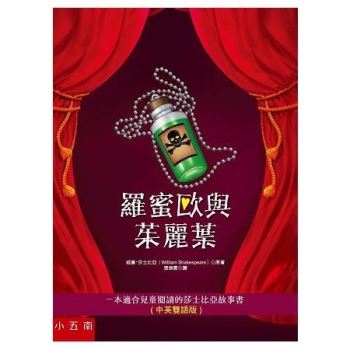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