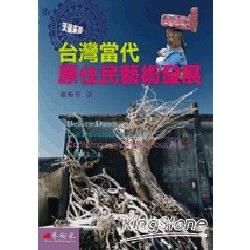新書介紹
本書是台灣第一本以藝術評論為基礎關懷的原住民藝術論著,並涉及人類學、博物館與文化研究領域。
同時爬梳歷史,以歷史背景鋪陳做為當下原住民藝術窘狀的基礎根源;並透過作品接合歷史血肉,分析台灣原住民藝術如何從族群藝術、「泛原住民藝術」發展到現代或個人藝術?藝術的功能,如何從生活藝術、觀光商品、藝術產業到純藝術創作?而在此變遷的過程中,原住民藝術的角色與價值又是為何?
本書試圖將當代原住民藝術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與困境做踏實的釐清、試圖揭開隔閡現實中的原住民藝術與社會大眾之間的虛幻幛幕,包括浮濫的天賦描述、原始的想像、差異的光環等。思考要如何讓這個社會更能深刻、敏銳地感受到原住民藝術所需面對的殖民障礙與現實困難。
作者簡介
盧梅芬1974年生
【學歷】
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1996-1999)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系(1992-1996)
【獲獎與經歷】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1999-)
〈認同與藝術表現:當代台灣原住民木雕藝術隱含之原住民化現象〉獲1999年「第一屆帝門藝術評論徵文獎」首獎
【策展經歷】
2003 部落的旋律?時代的脈動「回憶父親的歌:陳實、高一生與陸森寶的音樂故事」特展。主編《回憶父親的歌》繪本套書(共三冊),獲2004年行政院「優良政府出版品獎」。
2002 來自部落的聲音「微弱的力與美:當代台灣原住民創作的文化展現」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