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
──齋藤美奈子
重松清喜歡描寫的人物,都是一些隨處可見的市井小民。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中年男子(以及生活在現代的少年少女),這可以說是他一貫追求的主題之一吧!他獲得直木賞的作品『維他命F』就是由幾篇短篇小說所組合而成的形式,描述父子之間的迷惘。本書『流星休旅車』則是更深入去探討這個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描寫父子之間的溝通問題。
在『流星休旅車』中出現的三對親子─正確說來是父親和兒子。
故事的主角/ 永田一雄三十八歲。他的家庭成員有同年齡的太太和就讀國一的兒子‧廣樹。一家人住在東京郊外的大樓,過著表面上看似相安無事的生活。但不久,兒子廣樹卻開始性情大亂,妻子行蹤不明的外出也變得越來越多。加上他又正巧被公司解雇、意外失業。這一切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失控的呢?就在整個家庭即將面臨瓦解之際,一雄突然有「尋死」的念頭。
另一對父子是主角一雄和他的父親。一雄討厭自己的父親。他的父親是白手起家,靠著土木建築和放高利貸的事業而成功的商人。他的父親如今已經六十三歲了,罹患癌症末期、命不久矣,正在故鄉的醫院靠著注射點滴維持生命。一雄每個月會到醫院去探望父親幾次,其實他這麼做的目的,只是想藉探病的名義領取「車馬費」當生活費的補貼而已。
第三對父子是橋本先生和他的兒子健太。五年前,在他三十三歲那年,橋本先生開車行駛在信州高原時,因為失誤而迎面撞上對向的卡車,和當時年僅八歲的兒子,兩人當場死亡。
故事的開始就是由這對橋本父子開著休旅車載著一雄,穿越時光隧道,重返過去。因為橋本父子已經死了,所以說他們是幽靈。這對幽靈父子不但很友善,而且還對一雄家裡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們提議說要帶一雄去幾處對他而言「最重要的地方」。而一雄在不知道自己是生是死的情況下,被帶到一年前的某個地方,同時還遇到應該在跟病魔對抗的父親。他的父親也回到跟他一樣的年齡,兩人都是三十八歲。
雖然是荒誕無稽的幻想故事,但是『流星休旅車』卻能引人入勝,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稍微遠離故事,來談一點比較嚴肅的話題吧!
『流星休旅車』中所出現的三對父子,看似不同,其實卻十分相似。父親固然會為兒子著想,但其實卻完全不了解兒子的心意。兒子也對父親心存芥蒂(讀者到最後才知道,原來乍看之下這對感情很好的橋本父子,心中也隱藏著秘密。)因為我既不是父親也不是兒子,所以聽人家說:「『流星休旅車』是賺人熱淚的作品喔!」我雖然邊看邊擤鼻涕,但卻還是無法完全理解為人父親的心情(真是不好意思耶!)。不過,在我的想像中,或許社會上有很多類似這樣的父子吧!他們之間的關係性,與其說是來自個人的資質,倒不如說是源自近代社會病態的結構吧!
法國的社會史學家巴丁特夫人(Elisabeth Badinter)在她的著作『XY─男人是什麼東西』一書中,已經說明了這種情況。
<過了十九世紀中葉工業社會得以實現之後,男性必須一整天都待在工廠、礦山、辦公室等等家庭以外的地方工作才行。住在都市中的父親和小孩之間的互動明顯地減少。在孩子的眼中,父親總是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變成一種遙不可及的存在。(略)經過五十年之後,這個世界被二分為完全沒有交流的不同性質的領域。一是所謂私的領域,也就是由母親管理的家庭。另一個則是公共的職業領域,也就是只有男人的世界。>
日本的情況幾乎完全相同。尤其是在戰後的高度成長期之後,職場和家庭便被完全切斷。父子之間的距離也變得越來越遙遠。父親和兒子之間的不幸也由此拉開序幕。極端說來,在家中失去地位的父親,就只剩下兩種選擇。(A)為保持一家之長的尊嚴,炫燿自己的權威。(B)為討好孩子的歡心,扮演善體人意的爸爸。另一方面,因為和父親的生活圈(職場)完全脫離的關係,兒子無法從父親的身上找到自我認同的男性榜樣。到最後父親的形象就只剩下巴丁特夫人所說的兩選一,<不是難以親近的遙遠父親,就是沒有男子氣概讓人瞧不起的父親。>
<對兒子而言,父親就如同不懂得妥協、難以親近的神明一樣。面對這樣一位可怕的男人,兒子日後恐怕會如此描述他的父親吧!「我在家裡以外的地方做些什麼事,他完全不知道。他也從來沒有問過我有哪些朋友。記憶中他也從來不關心我在學校的成績。」如此一來,孩子在威權主義的父親和態度冷淡的母親影響之下,長大後就會變成「父愛非比尋常」的父親。然而,這樣的父親因為太過善體人意了,往往被妻子給騎到脖子上去,結果反而會被孩子瞧不起。>(『XY─男人是什麼東西』)
就如同『流星休旅車』中的兩位父親,阿忠和阿雄一樣。
『流星休旅車』一書之所以如此「引人入勝」,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有社會學的根據,因為本書所描寫的,的確是近代父子的典型關係。
話雖如此,不過,這本書之所以能夠打動人心,應該還是要歸功於故事本身所具有的魅力吧!
本書中的某些情節會讓人聯想到電影『回到未來』。或是狄更斯的小說『聖誕頌』(描寫一位倫敦的吝嗇商人司庫吉,如何苛待他的夥計鮑伯,在聖誕前夕司庫吉的友人馬雷的鬼魂找上他,帶他去看鮑伯的家庭。他們家雖然貧窮但卻很快樂。於是在聖誕節早上,司庫吉醒來後悔自己以往的所作所為,因此大大改變,開始樂於助人。)畢竟期望能夠返回過去、讓一切能重新來過,這是人類永遠的願望。因此,便創造了以穿越『時光隧道』為主題的各種寓言或是科幻小說。本故事中帶領一雄回到過去的橋本先生,就像是狄更斯小說中出現的幽靈一樣。而載著他穿越時空的那輛奧迪賽,就像是電影『回到未來』裡面的時光機器。
不過,『流星休旅車』並不是寓言。它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現代故事,其證據之一就是它完全否決了「重新來過」的可能性。它不像電影『回到未來』裡面的主角米高福克斯有個快樂的結局。也不像狄更斯小說的主角最後可以悔過自新。……
流星,時光休旅車本文
有位既愚蠢又可悲的父親。
那是發生在五年前的事。
一則刊登在報紙社會版上的小小新聞。
標題是<全家首次開車出遊的悲劇>-一家三口開車出遊行經信州高原時,因為車速過快來不及轉彎,結果迎面撞上對向的卡車。母親雖然即時保住一命,不過父親和兒子卻當場死亡。據說開車的父親才剛在一星期前領到駕照而已,而買新車交車的隔天便發生了這起交通意外事故。
這種通常在早晨看完報紙之後隨即遺忘的小小悲劇新聞,卻奇妙地一直縈繞在我的心頭。起初我還發出笑聲說:「怎麼會有這種父親呢?」但闔上報紙之後,卻不禁感到有些難過。
畢竟發生這起意外事故的一家人,他們的家庭成員幾乎和我家一模一樣。
我今年三十三歲,我的太太-美代子跟我同年。我們還有一位八歲、就讀國小二年級的獨生子-廣樹。
如今回想起來─那段時期可以說是我們家的黃金時代。
說不定當時的我正處於人生的顛峰期。
*
因為交通意外事故而喪生的那位父親名叫橋本義明,他的兒子名字叫健太。
橋本先生和健太以五年前事故發生當時的模樣出現在我面前,看來在他們兩人所處的世界裡,時間是停止不動的。
橋本先生以河流和小船為比喻為我解說。他說浮在河面上的小船,沿著上流順流而下,然後再逐漸流向大海-那是我們一般人所生活的時間。至於橋本先生和健太兩人的小船,則因為五年前的那場意外而失事擱淺在河裡,再也無法駛向大海,當然也無法逆流而上。既無法浮出河面也無法沉入河底,於是只能一直停留在原處,只有在偶然的機遇下會和一些迷途誤闖擱淺處的小船不期而遇。
我們不斷地開車兜風,也不知道經過多少天的時間,總之那是一趟相當不可思議的兜風之旅。
橋本先生開著箱型車,以滑行般的速度在夜晚的道路上奔馳。
「如果是現在的話,就絕對不會再發生那種愚蠢的交通事故。」
橋本先生說著,語氣中流露出些許的懊惱。
*
在開車途中,我曾經問過橋本先生一件事。
「為什麼會挑上我呢?」
橋本先生邊笑邊回答我說:「那是因為你有尋死的念頭啊!」
「對於那種事,我們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喔!」
坐在駕駛座旁的健太也開心似地說道。
*
希望在今夜就此死去。
如果你也曾經有過這種念頭的話,建議你不妨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裡,等最後一班電車開走後,在車站前面稍作停留。要是你發現有一台酒紅色的舊型奧迪賽(Odyssey)停在那裡的話,希望你能稍待片刻。
要是橋本父子喜歡你的話-看來選擇權似乎是在健太身上,車子便會靜靜發動,停在你的面前。
駕駛座旁的車窗搖下,那位探出頭來的少年就是健太。
「你遲到了!」健太應該會對你說。
車門的自動鎖解除。
「快點上來吧!我們一直在等你。」
健太雖然有點臭屁,不過卻是一位活潑開朗的少年。
你肯定會不由自主地打開車門。因為與其說是出自自由意志,倒不如說是受到某種力量的牽引。
當你坐進三排座位的第二排,關上車門之後,車子便開始發動。
勸你最好不要詢問要去什麼地方。因為就算你問了也是白問。畢竟健太只會露出惡作劇般的笑容,並不會回答你的問題。而橋本先生則是默默不語,猛踩油門加速行駛。至於你則既不會覺得奇怪,也不會感到害怕。不對,應該說甚至連「奇怪」的感覺都沒有。
不久,窗外逐漸變得明亮起來。
等你回過神來的時候,發覺你置身在一處令人懷念不已的地方-你正站在一處對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場所。
就如同我一樣。
1
那天晚上,我感到疲累不堪。
甚至連下定決心尋死的力氣都沒有,渾身散發著些許的酒味,一面坐在搖搖晃晃的末班電車上,一面心神恍惚地思索著。
如果能夠就此死去的話也無所謂。
我發出冷冷的笑聲。望著自己倒映在玻璃車窗上的模樣,打從心底感到了無生趣。想不到自己竟然變成了會發出那種笑聲的男人,不免感到一陣惆悵,竟又再度發出同樣的笑聲。
抵達羽田機場時已經接近晚上九點,我從單軌電車的濱松車站下車,順便在車站前找尋還在營業的燒烤店。先搭山手線到新宿,出站之後,趁轉搭私鐵電車之前,先到附近的小吃店小酌一番。
直到剛剛為止,藉著微醺的酒力我一直都在打瞌睡。雖然才短短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我卻睡得十分深沉,宛如掉進了黑暗的無底深淵一般。
要是能夠就此長眠不醒的話,不知道該有多好。星期天的晚上,坐在末班電車空空蕩蕩的長椅子上氣絕身亡,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要說心中絲毫沒有任何遺憾或眷戀的話,那是騙人的。不過,我覺得能帶著那樣的心境離開人間,說不定反而是一種幸福。
電車在每個小站停靠,一面讓寥寥無幾的乘客上下車,一面緩緩開往我所居住的城市。因為是每站都停的慢車,所以從新宿到東京的西郊,足足要花上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要是自己開車的話,只消不到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進入神奈川縣,那是一處規模相當龐大、幾乎可以稱之為新市鎮的住宅區。從車站到我家必須徒步十五分鐘越過一處陡峭的坡道。通常白天工作所剩餘的那一丁點力氣,走到這個坡道時便已經消耗殆盡。
或許每次進家門時說:「我回來了」的我,往往只剩下一付軀殼而已。我懶得去想那些艱澀的問題。我所想要的,就只是家人的笑容、遲來的晚餐、洗個熱水澡和上床睡覺而已。至於其他多餘的事,我一概不想承擔。我不知道對美代子說過多少遍類似這樣的話「我無所謂。」「一切就由妳決定吧!」我甚至連想都沒想,就不由自主地脫口而出。
結果現在報應終於來了……我輕輕地閉上眼睛,阻止自己繼續胡思亂想。
一旦開始反省或感到後悔的話便沒完沒了,況且我早已過了那個階段。如今無論我再多說什麼或多想什麼,都已無濟於事。更何況我早已無心採取任何的補救措施了。
既沒有夢想也沒有希望。
記不得這是兒時的歌詞,還是小故事或漫畫裡面的台詞。長年所累積下來的疲勞,讓我的雙臂只要稍微轉動一下便會感到隱隱作痛。根據醫生的診斷說,很有可能是四十肩提早報到。總之,我疲累的肩膀就像是承載著一付無法擺脫的千斤重擔一樣。
電車還剩下一站,就接近我所居住的城市。
其實就算死了也無所謂。我交叉雙臂、語帶嘆息地說道。
我已經疲累不堪了。再也無法忍受了……。
我像個孩子似地在心中喃喃自語,卻聽見有威脅恐嚇的聲音回答我說:「要死就去死啊!少在那裡囉唆了!」
電車離站之後速度逐漸加快。街上的燈光也已經顯得疏疏落落。想必再過不久電車就要經過多摩川上的鐵橋。因為這裡是一個分界線,一旦過了這裡之後氣溫便開始驟降,所以車窗蒙上一層白白的霧氣。已經是秋末時節了。今天醫生告訴我說,家鄉的父親恐怕捱不過這個年了。
我當天往返故鄉。從羽田機場搭飛機前往的話,只要不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稱之為「歸鄉」之旅似乎有點短暫。從機場租車,再驅車前往面向瀨戶內海的故鄉城市,所花費的時間反而更長。
這半年以來,我大概每個月會回去二、三次。剛開始是利用週休假期回去住宿一晚。但近來由於感覺在空空蕩蕩的家中和母親四目相對心情太過沉重,於是到醫院探病之後便直接返家。
每次返鄉,都會發現父親的身體日益衰弱。記得夏天我去探病的時候,在母親和看護的幫助之下,父親還能撐起身子坐在病床上。但今天他從頭到尾都一直躺在病床上,用塌陷的眼神茫然地注視著天花板。
即使沒有把病情告知本人,但相信他本人也早已有所察覺才對。父親所罹患的是癌症。而且已經從肺部開始轉移到胰臟、腎臟、肝臟,甚至蔓延到腦部。醫生說要是病人的背部和頭痛得非常厲害的話,就會考慮替病人注射嗎啡。其實父親在五月住院時,醫生就已經診斷說他的情況是癌症末期,恐怕熬不過這個夏天。
然而,父親卻安然地度過夏天。他原本就是一位待人和律己都非常嚴格的人。日益虛弱的身體讓他感到焦慮,整個人變得更加孤僻、動輒大發脾氣。不但辭退了好幾名的看護,甚至連在一旁照顧他的母親和妹妹智子也受到了波及。他就這樣茍延殘喘了半年。
父親的生命力讓醫生嘆為觀止。母親佩服似地說:「因為你爸爸是個韌性很強的人。」而小我三歲的智子則模仿父親的樣子笑著說:「像我這麼有氣魄的人,怎麼可以死在這種地方呢?」的確,父親今年也不過才六十三歲而已,相信一定還有許多他想做或非做不可的事情在等著他去完成。
父親是靠白手起家成功的。他是從開土木建築店起家的,擁有多家的公司。在我中學時代他最賣力的事業就是放高利貸─也就是開地下錢莊。
有些時期父親的事業蒸蒸日上,但也有些時期他無論從事什麼事業到最後都一敗塗地。有些公司的確讓他一攫千金;但也有些公司父親只是個掛名的董事長而已,實際的經營權卻掌握在別人的手中。自從泡沫景氣瓦解之後,他的事業便一直在走下坡。智子的說法是:「還不是因為老哥你擺明不肯繼承老爸的事業,所以爸爸才一下子蒼老了許多。」
不知道是否真的如此。不過,自從我上了中學之後,幾乎就沒有跟父親單獨說過話了。
父親把女婿-智子的先生伸之,當成是他事業的繼承人,自從過了六十歲之後就逐漸把事業轉交給他。伸之年約三十五歲,是京都大學法學院畢業的,加上又曾經在貿易公司待過,他優異的表現遠遠超過父親的期望。相較於做事態度向來都採取勇往直衝的父親,伸之的個性則比較擅長守成,所以他是最適合帶領公司渡過泡沫經濟瓦解後長期不景氣的接任人選。父親也非常信任他,對他有更大的期望,甚至還向當地的國會議員介紹說他是「自己的兒子」。
想不到過去如此深受他信賴的伸之,如今卻被禁止來病房探病。
不知道究竟是因為癌細胞轉移到腦部的關係,還是因為藥物副作用的關係,父親從夏天開始就突然變得猜疑心很重,甚至還會用憎恨的眼神瞪著親人。有時候疑神疑鬼的程度幾乎接近精神錯亂。不但把像親人般照顧他的看護當成小偷把人家辭退,甚至連擔任公司二十幾年的秘書長西山先生都認不出來,還口出穢言怒罵人家,逼得對方辭職。
對於他一向信賴的伸之,從上個月開始說他:「那傢伙想要奪取我的公司。」就算伸之到病房來探視他,他不是不發一語,就是把頭轉向一邊,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其實他早已沒有那個力氣了,不過據說有時候他甚至還想拿裝白開水的鴨嘴壺扔他呢。
至於我的話,父親完全沒有說過我什麼。對於我來探病他既沒有露出開心的表情,也沒有不高興。我幾乎沒有跟他說話。與其說是去探病,感覺上還比較像是去掃墓。我只是茫然注視著父親緩緩死去。
記得在初秋時,智子曾經建議我推著輪椅帶父親到醫院的中庭散步。父親當時只是跟我說了二、三句不著邊際的話而已。而我也只說了幾句像是「波斯菊很漂亮」或「今天的海面風平浪靜」等等無關痛癢的話。原本應該推著父親沿著中庭的歩道散步一圈才對,但我卻直接從中間的小徑穿過,所以只走了半圈而已。我們一回到病房,母親和智子似乎顯得有點失望,發出無力的笑聲。那一天是父親最後一次走出病房的日子。
不知道父親還能夠支撐多久。
為什麼還要活下去呢?
躺在病床上,只能吃流質的食物和注射點滴,連大小便也必須仰賴母親和妹妹的幫忙。儘管如此,為什麼還要活下去不可呢?
父親會主動跟我說話,通常是在我差不多準備要離開病房的時候。
今天也一如往常。
「你有在工作上好好打拼嗎?」
父親用沙啞、微弱的聲音說道。「要趁著年輕力壯的時候好好打拼才行喔!」他下巴上沒刮的白鬍子輕微地晃動著。
說得也對。我回以淡淡的微笑。
「美代子和廣樹他們都還好吧?」
「他們都很好。」
「替我問候他們。」
「嗯……我知道了。」
當我正準備從摺疊椅上起身時,父親向母親喊了一聲「喂」,然後以眼神示意床旁邊的櫃子。這也是慣例。直到夏天為止他還可以自己走到那裡打開櫃子的抽屜。到秋天中旬時,他還能夠用手指示。這遠比醫生給我們看的那些數字、圖表或胸部X光片要清楚許多,可以明顯地看出父親的身體日漸衰弱。
母親從抽屜裡拿出一個印有公司名稱的咖啡色信封。『丸忠公司』-父親的名字叫做忠雄,把忠字用圓圈圈起來,就是公司的徽章。
信封上還寫著「車資」的字樣。裡面裝有五張一萬日圓的鈔票。扣掉我往返的機票錢和租車費用,還綽綽有餘。
我默默地收下。把信封放進夾克內的口袋之後,奇怪的是接下來的動作卻變得有些慌張,我草草告別之後隨即轉身離開病房。
一坐進停在停車場內的車子,在發動引擎之前稍微閉目養神。我慢慢地吐氣,把懷著愧疚的氣息慢慢吐出。
難道父親絲毫沒有起疑嗎?這半年以來美代子和廣樹從未來醫院探望過他。相信今後─恐怕連他的喪禮也不會去參加吧!
我的家庭已經完全粉碎了。恐怕再也難以破鏡重圓了。如果沒有父親給我的「車資」,我甚至無法返鄉。說句老實話,我之所以返鄉的次數如此頻繁,其實是為了扣除「車資」之後所剩下的餘額。…….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流星,時光休旅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8 |
二手中文書 |
$ 199 |
日本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流星,時光休旅車
如果還有機會回溯時光、
回到過去,破碎的人生還有沒有機會……
日本直木賞作家 重松清撼動心靈長篇力作!
日本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四顆半星激讚好評!
日本讀者「真希望能更早讀到這本書……」淚流不止,感動推薦!
『流星休旅車』,說的是有關於父子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永田一雄,三十八歲。他的家庭成員有同年齡的太太和就讀國一的兒子‧廣樹。一家人住在東京郊外的大樓,過著表面上看似相安無事的生活。但不久,兒子廣樹卻開始性情大亂,妻子行蹤不明的外出也變得越來越多。加上他又正巧被公司解雇、意外失業。就在整個家庭即將面臨瓦解之際,一雄突然有「尋死」的念頭。
也在這時候,他遇見了一對開著休旅車到處兜風的幽靈父子。
他坐上了那輛酒紅色的休旅車,等他回過神來的時候,發覺自己竟置身在一處令他懷念不已的地方──一處對他而言非常重要的場所……
作者簡介:
■作者|重松清(Kiyoshi Shigematsu)
1963年出生於日本岡山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自由作家。
1991年以《ビフォア•ラン》在文壇展露頭角。1999年,以《ナイフ》(中譯本:《刀》)獲得第14屆坪田讓治文學賞,同年又以《エイジ》獲得第12屆山本周五郎賞,2001年以《ビタミンF》(中譯本:《維他命F》)獲得第124屆直木賞。
譯者簡介:
■譯者|蕭照芳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日本九州大學文學碩士。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業譯者。生性閑散,崇尚老莊思想,熱愛自由和旅行。譯有漫畫《聖傳》、小說《你的朋友》、《泥土裡的孩子》、《世紀末的鄰人》教養書《靈魂自由人》、《走進小孩的內心世界》。實用書《咖啡吧台師傅教戰手冊》、《就愛咖啡好滋味》等等。
章節試閱
解說
──齋藤美奈子
重松清喜歡描寫的人物,都是一些隨處可見的市井小民。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中年男子(以及生活在現代的少年少女),這可以說是他一貫追求的主題之一吧!他獲得直木賞的作品『維他命F』就是由幾篇短篇小說所組合而成的形式,描述父子之間的迷惘。本書『流星休旅車』則是更深入去探討這個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描寫父子之間的溝通問題。
在『流星休旅車』中出現的三對親子─正確說來是父親和兒子。
故事的主角/ 永田一雄三十八歲。他的家庭成員有同年齡的太太和就讀國一的兒子‧廣樹。一家人住在東京郊外的大樓...
──齋藤美奈子
重松清喜歡描寫的人物,都是一些隨處可見的市井小民。尤其是生活在現代的中年男子(以及生活在現代的少年少女),這可以說是他一貫追求的主題之一吧!他獲得直木賞的作品『維他命F』就是由幾篇短篇小說所組合而成的形式,描述父子之間的迷惘。本書『流星休旅車』則是更深入去探討這個主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描寫父子之間的溝通問題。
在『流星休旅車』中出現的三對親子─正確說來是父親和兒子。
故事的主角/ 永田一雄三十八歲。他的家庭成員有同年齡的太太和就讀國一的兒子‧廣樹。一家人住在東京郊外的大樓...
»看全部
作者序
〈流星,時光休旅車_後序〉
文庫版後序
我認為在我的幾部作品之中,有些是當上「父親」之後才寫得出來的。『流星,時光休旅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這本書是在我身兼「父親」和「兒子」雙重身份的時期,最想寫下的一部作品。
我是在二十八歲的時候當上「父親」的。五年後,第二個小孩出生。兩個小孩都是女孩子。
從那個時候開始,聊起往事的次數突然急遽增多。那些已經逐漸遺忘的年少往事又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說句比較露骨的話,或許這就證明自己真的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老頭子。不過,換一種比較矯情的說法是,自從成為「父親」...
文庫版後序
我認為在我的幾部作品之中,有些是當上「父親」之後才寫得出來的。『流星,時光休旅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這本書是在我身兼「父親」和「兒子」雙重身份的時期,最想寫下的一部作品。
我是在二十八歲的時候當上「父親」的。五年後,第二個小孩出生。兩個小孩都是女孩子。
從那個時候開始,聊起往事的次數突然急遽增多。那些已經逐漸遺忘的年少往事又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中。說句比較露骨的話,或許這就證明自己真的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老頭子。不過,換一種比較矯情的說法是,自從成為「父親」...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重松清 譯者: 蕭照芳
- 出版社: 唐莊文化 出版日期:2010-07-31 ISBN/ISSN:978986711850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6頁
- 類別: 中文書> 世界文學> 日本文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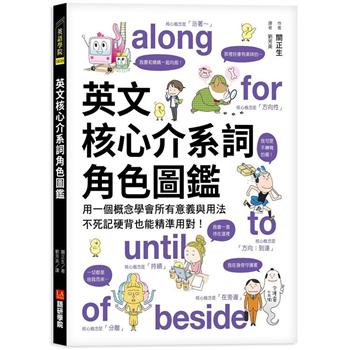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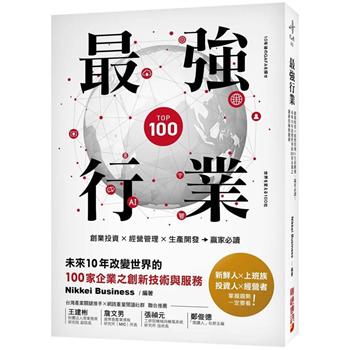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