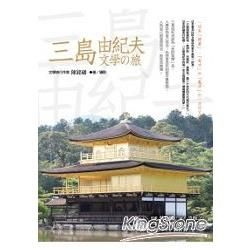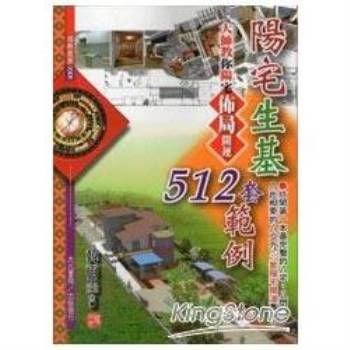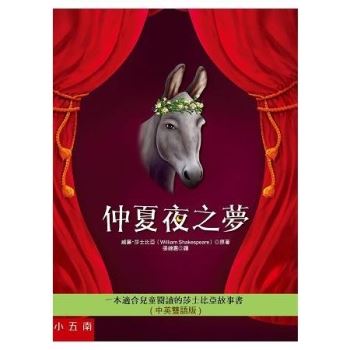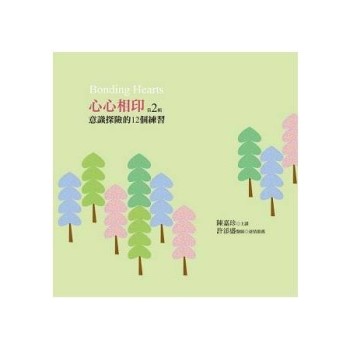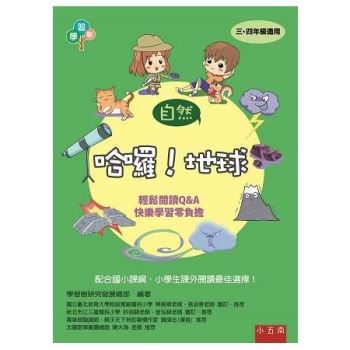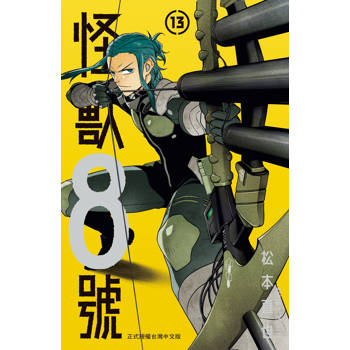推薦序
寫作人生最忠實的完美結局
吳祥輝
行動派的作家最吸引青少年時代的我,就像描述人和荒野或海洋的小說,通常比人和大地的故事更讓我著迷。三島由紀夫因此而進入我的心中。
青少年的閱讀之心或許比較傾向靈性的感應,對追尋自我生命意義,不害怕死亡的作家總是帶著崇敬之情,無關乎抉擇的內容,或者是病態或健康。
國家心靈和作家心靈越到深處越衝突激盪不停。三島由紀夫是最強烈的一種典型。從作家理性看,他崇尚戰前的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未來對他已經越來越遙遠,而非越來越近。選擇切腹自殺作為封筆之作,恐怕就是他寫作人生最忠實的完美結局。
(吳祥輝,作家,著有《拒絕聯考的小子》《芬蘭驚艷》《陪你走中國》等。)
推薦序
虛妄的死亡美學
許悔之
評論家認為三島的文學充滿虛妄的死亡美學,也即滅絕。除了《金閣寺》彰顯這種美學之外,他作品中的《豐饒之海》四部曲,從《春之雪》到《天人五衰》,以本多繁邦這個具有偷窺習慣的「說故事者」的角色,把幻滅人生的意識表達得最為具體。
三島挑釁美,撩撥美,他小說中的男主人大抵為俊美男子,但最終命運都成為作者筆下美的滅絕者。他創造美,棲息美,毀滅美,他心中的美盡是死亡;這可從《豐饒之海》中的松枝清顯、飯沼勳和安永透,在璀璨的二十歲生命,走進死亡、自殺和目盲看出端倪。
美的靈魂被三島擾亂了,縱令他用華麗的文字,截取美的瞬間景色、美的人物,最後仍不免以死傳述滅絕。執拗追逐滅絕幻影的人,三島的作品是美學和死亡交錯的舞台,更是他文學最本源的動力。
(許悔之,詩人,著有《我佛莫要,為我流淚》《有鹿哀愁》《遺失的哈達》等。)
推薦序
男體告白
張典婉
年少時,初識三島由紀夫是在一群青春的男同學間,才脫離童年與尷尬的少年變聲期,進入了可以成為男人的喜悅,青春的肉體有荷爾蒙滿溢的驕傲,有些人在不同的女子間擺盪追逐,學習成人世界中的愛情遊戲。
有些沉溺男體,散發鬼魅的男生,卻是三五成群捧著《假面的告白》,或是《金閣寺》的不同版本,討論話題中有著男體對同性間憐愛的疼惜。
在他們交談中,我也懵懂地了解三島由紀夫的青春情慾的性別告白。一九七○年,三島由紀夫切腹的新聞震驚了全世界,在這些視他為偶像的男體眼中,竟都是有著一樣落寞的眼神。
直到很多年後,帶著朝聖的心去到金閣寺,原想找尋美得要毀滅的金色天空,可是太多的觀光客,只想讓人快快逃離現場,突然想起那些年少時期的男體告白,可還依然如昔。
(張典婉,作家,著有《太平輪一九四九》《台灣客家女性》《苗栗山水》等。)
推薦序
雨水滴心寒,意志溢海岸
路寒袖
三島以死亡或滅絕為主軸的眾多文學創作中,《潮騷》是少數勵志性的寫實作品,雨水滴心寒,意志溢海岸。小說描述長相俊挺的年輕漁夫久保新治和船家獨生女宮田初江,艱辛曲折的戀愛過程。情節簡單,卻充滿希臘式的田園詩情風格。
作者突破個人自戀式的幻滅寫作技巧,從而讓女主角勇於衝撞世俗成見,鄙視財富,執著追求愛情,拒斥在貧窮與財富對應下所產生的階級偏見。全書不脫三島美學的一貫作風,溫柔的初江和溫暖的新治,醜陋的安夫和僻性乖張的千代子,相互交織一幅凡間通俗的愛情故事。
性格多變的三島,運用作品中難得溫暖色澤的《潮騷》,歌頌伊勢灣神島村漁民的純樸個性,如此明朗的文體,正是他反現實主義的文學佳構。
(路寒袖,詩人,著有《春天的花蕊》《憂鬱三千公尺》《我的父親是火車司機》等。)
推薦序
毀滅與至美的詭異並存
劉智濬
將絕美的金閣寺縱火焚毀,是三島由紀夫及其筆下人物自我救贖的必經之路?毀滅與至美如此這般的詭異並存,挑戰著《金閣寺》讀者心靈的感應深度與廣度,必須承認,我這個異國、異代的讀者,始終無法真正完全融入其中。
侯孝賢《悲情城市》曾有這樣一幕:最終為國府軍隊殺害的台灣知識份子寬榮,生前提到日本人自殺行為背後的櫻花精神──在生命最美的時候隨風離枝,這是全片台灣男子,除了年邁與發瘋者,最後全都殞滅的命運的預告。
這大概是我可以理解的極限了,但是距離《金閣寺》的深邃本質,依然十分遙遠;曾經繞行於秋天的金閣寺庭園,金碧輝煌與璀璨楓紅相映,然而,我只感受到寂靜之美,那個嚴重口吃的僧侶的焚燒之舉與眼前的美景如何連結?日本文化的某些面向,在那一刻,突然陌生起來。
(劉智濬,台灣文學博士,中台科技大學教授)
作者序
風華絕代的文學之美
陳銘磻
我怕怎麼掉下淚水的記憶都會消失,所以才把心情寫下來。
二○一一年,時序進入春季,我正積極而緊密的忙碌搜集、整理和寫作《川端康成文學的旅》、《三島由紀夫文學的旅》、《夏目漱石文學的旅》三書,不料寫到川端「生並非死的對立面,死潛伏於生之中。」與「自殺而無遺書,是最好不過的了。無言的死,就是無限的活。」的淒美文字,恰如「我彷彿只有腳離開現實,遨遊於天空中了!」這時,客廳的電視新聞主播正聲嘶力竭的報導日本東北地區的宮城縣和茨城縣,遭逢九級的強烈大地震,同時引捲起二十幾公尺高的大海嘯,把鄰近城鎮淹沒成一座座空寂死城,死傷和失蹤人數遠超過萬人以上。
主播急促的聲音,瞬間喚醒我的知覺,我即刻從川端生死美學的文字裡跳脫開來,焦慮的走到螢幕前,睜眼面對滾滾浪潮把臨海市鎮吞噬襲捲的驚悚畫面,不忍卒睹的心情,一剎時,腦海中立即浮現出曾經到訪過,仙台市樸實的街景,以及松尾芭蕉俳句裡描繪的松島美景;這一場世紀大浩劫不僅淹沒東北地區難以數計的住民生命,就連當地的歷史、文化也一併被吞沒掉了。難忍苦楚的心,豈止痛字,天地無情,何能言語?
被松尾芭蕉讚譽形容:「松島呀!啊!松島呀!」的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位於松島灣,與樸實的仙台同屬於宮城縣。仙台是日本幕府時代著名的「獨眼龍」將軍伊達政宗,自十七世紀初統治這塊土地時所建立的古城,伊達家族以「青葉城」為根據地,在此建立起富有藝術與文學氣息的城市,時日一久,城下町開始繁榮富庶起來,仙台因而發展成為東北地區的文化中心。其中,仙台城跡、大崎八幡宮、東照宮,以及昔日治理仙台的領主,相關的古寺廟和神社四處林立。
想到宮城的災難,不免想起昭和初期的詩人、童話作家宮澤賢治的詩作(不要輸給雨):
不要輸給雨 不要輸給風 也不要輸給冰雪和夏天的炙熱 保持健康的身體 沒有貪念 絕對不要生氣 總是沉靜的微笑 一日吃四合的糙米 一點味噌和青菜 不管遇到什麼事 先別加入己見 好好的看 聽 瞭解 而後謹記在心不要忘記 在原野松林的樹蔭中 有我棲身的小小的茅草屋 東邊若有生病的孩童 去照顧他的病 西方若有疲倦的母親 去幫她扛起稻桿 南邊如果有快過世的人 去告訴他:不要害怕 北方如果有吵架的人們 去跟他們說:別做這麼無聊的事情了! 旱災的時候擔心的流下眼淚 夏季卻寒流來襲 不安的來回踱步 大家說我像個傻子 不需要別人稱讚 也無需他人為我擔憂 我 就想當這樣的人啊。
悲天憫人的情懷,寓意深遠,使人讀後動容不已。
地震尚未停歇,海嘯依舊滾滾而來,天地如物換星移,倏忽變色,我的視線黯然回到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的死亡美學裡,試圖從這些文學家的作品尋找他們對於「滅絕」的意識。
川端的文學作品,不僅流露出《源氏物語》所表現的王朝貴族,象徵冷艷美的官能性色彩,以及他那來自時代與民族性所支配的美學態度,正是他戰後的作品具體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心理困惑、迷惘以及沉淪的世態。他還將日本的悲哀、時代的悲哀,以至於自己的悲哀,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悲哀美」和「滅亡美」。尤其承受西方「悲觀哲學」與「神祕主義」的衝擊,川端在日本傳統美學的思維裡,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從而也找到東西方世紀末思想的匯合點。這即是他十分顯著的頹廢情調。
川端自青少年時期即已從心中累積的世界觀、人生觀的過程,接觸到不少死亡事件,他在日常生活裡常「嗅覺到死亡氣息」,進而產生對死亡的恐懼,他感受到生是在死的包圍之中,死是生的延伸,生命是無常的,好似「生去死來都是幻。」因而,愈加著力於從幻覺和想像中追求「妖艷的美的生命。」以及「自己死了彷彿就有一種死滅的美。」
看待「滅絕之美」為美的極致,讓川端在人世間七十三年的苦海生涯後,選擇口含煤氣管自盡身亡,成就自己對於物的「有」與「無」的界定,誠如他欣賞的印度哲人泰戈爾的思想:「靈魂的永遠自由,存在於愛之中;偉大的東西,存在於細微之中;無限是從形態的羈絆中發現的。」
一九七○年十一月,以《金閣寺》一書揚名國際的三島由紀夫,在東京市�谷自衛隊辦公室切腹自殺後,不少知名作家趕到現場,但只有川端康成獲准進入探望。三島之死,川端深受刺激,曾對學生表示:「被砍下腦袋的應該是我。」
同樣追求「絕美」人生的三島,早年的個性潛沉著強烈的陰柔氣質,他厭惡劍道,甚至厭惡劍道砍擊時所發出的聲響。直到年近三十歲時,他倏地感覺自己對於美的強烈憧憬,開始上健身房運動及游泳,甚至勤習劍道,將年幼以來即孱弱的身體改造得更加強健,期使自己不再為虛弱的肉體感到頹喪與自卑。這種追逐美的心態,與他後來潛心撰寫的長篇名著《金閣寺》有所關聯,這本書中的主角就是一個自慚於口吃的猥瑣,卻又極端崇尚極致之美,導致內心扭曲與抱持幻滅心理的少年,一心想要摧毀「美的金閣寺」。這一點,可以說是三島在現實中的想法,這種意識又跟他的創作內容與華麗的文字互相呼應。
他在《金閣寺》一書寫道:「金閣知道,人生中,化身於永恆的瞬間,雖然能使我們陶醉,但與之此時的金閣化身為瞬間的永遠,相較起來,就很微不足道了。永遠存在的『美』,也正是在這時候阻撓我們的人生,搗毀我們的人生。生存中所顯示的驚鴻一瞥的瞬間美,在未遭荼毒之前,是脆弱得不堪一擊的,它立刻就崩潰消失,隨之,生存本身也暴露在滅亡的淡褐色光芒下。」
三島的一生充滿無數矛盾,他的死使他從難以自拔的矛盾中得以徹底解脫,更或者說,他的死使他一生都不曾安寧過的靈魂終於獲得安息。這也許即是他心中「永遠存在的美」吧!
相較於用「殉死」來完成心中「美的追求」的川端和三島,以寫作《我是貓》、《草枕》、《少爺》和《夢十夜》等書成為日本文壇巨擘的夏目漱石,情況則非如此。四十九年人間生涯的後半生,屢受神經衰弱症和胃潰瘍困擾,卻仍執意文學救社會、救國家的夏目曾說:「在這裡我決定,將從根本上解釋『何謂文學』的問題。同時我下決心,利用今後一年多的時間去研究這個問題,從而把它當做該研究的第一階段。我把一切的文學書籍都收拾在行李底層,已經把自己關在一家租屋裡。我之所以要通過閱讀文學書籍來知道何謂文學,是因為我相信以血洗血的手段乃為有效。我發誓,一定要追究文學到底產生於怎樣的心理需要,因而在這個世界生成、發達和頹廢的。也發誓一定要追究,文學到底產生於怎樣的社會需要,因而存在、興隆和衰亡的。」
他的文學尊嚴讓他坦然拒絕接受日本政府授予的博士稱號。一九一六年因胃潰瘍去世,臨死前,他同意將自己的腦和胃捐贈給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他的腦至今仍保存在東京大學。一九八四年,他的人像被印在一千元的日幣上。
選擇這三位同樣就學與畢業於東京大學的文學家,做為我個人「近代日本文學家的文學之旅」的對象,一方面源自於先前完成日本古典小說雙璧《源氏物語》和《平家物語》的文學之旅寫作與出版,更覺需要從被文學評論家形容為地地道道是《源氏物語》一貫傳承下來的日本典型作家,川端康成坎坷的一生,卻運用其敏銳心靈,洞察人生的生死場,然後寫下一行行美麗與哀愁的雋永文學作品,留予後世傳承典範的熱愛中,尋索意味。另則,究其遠因,自然是來自年少時代因喜愛而瘋狂閱讀這些人的作品,以及經由這三位文學家的名著改編拍成的電影,並受其深刻影響的緣故。
從事日本文學旅行的活動多年,每回前往日本旅遊,特別喜歡走訪具有歷史與文學象徵的地景,文學與文學家在日本的地位崇高,因此,關於以文學或文學家為主體的文學地景也跟著特別豐盛,我也就相對討了便宜,從中獲取更多研究資源與寫作材料。無論是《川端康成文學的旅》、《三島由紀夫文學的旅》或《夏目漱石文學的旅》,三位文學家著作裡所敘述或描繪的地景,我曾經多次走訪,如川端《伊豆的踊子》中的伊豆天城山、三島《潮騷》中的三重鳥羽和夏目《少爺》中的松山道後溫泉等,我在這些文學地景裡感受三位文學家取材創作的心思與意識,從而承歡他們在作品中所欲傳達的人生百相的悲喜特質。
依循三位文學家的出生、成長、創作、作品,乃至於辭世的地景寫作,我在這三本書裡,以一個欣賞者的角色,心陷其中,輕悄走過,領受風華絕代的文學之美與文學旅行的風雅之實。
最終,仍需感謝多位作家、學者和教授等好友,誠心推薦這三本書。更期盼讀者能藉由這些名家的推薦,從我的「文學旅行」中閱讀三位日本文學家淒美的人間生涯,與幽玄、蕭索或華麗的創作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