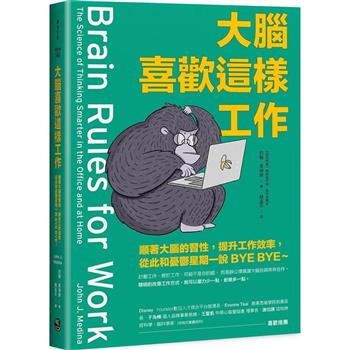作為一個卑微的旅人,我沒有能力詮釋我旅行過的世界,我只能觀察、記錄、理解,試圖參與。我也清楚的知道:無論我是否安全抵達我的目的地,我都已經回不去了。——胡晴舫
香港中環的一位婦人,點了一杯熱咖啡和中式炸豆腐,配了一小碟辣椒蘸醬,作為她的下午茶。——你應該驚奇嗎?『香港是個國際化大都市,炸豆腐當然可以和著熱咖啡下肚』。我的朋友說。沒問題,我收起愚蠢的表情。
胡晴舫看到這一幕,最後總結到:食物,成為最後一種辨識文化的方法。你對異質文化的容忍程度有多高,端看你對陌生食物的接受態度。
火車進入巴黎市郊時,許多巴黎人跳馬背式的越過捷運票口。我的朋友滿懷浪漫的說,『瞧!法國人就是這樣自由不拘!』而胡晴舫看到的是:旅人帶著他的偏見上路,有些舊偏見被印證,成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見。經由旅人的闖入,則影響了沒有離家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或,另一面的偏見。
這顯然不是一本坊間常見的私人旅游記錄,而是透過旅行現象窺視本質,如詹宏志先生所評價的,是作者對旅行和旅人(包括她自己)的行為和意義加以反省的書。她表達了對時下流行觀念的質疑,也悲觀的認為文化在旅游市場裡逐漸櫥窗化,成為一種能夠媚俗的商品。所以,你不要忘記了,峇里島當地人,是因為旅人的闖入,才搖身變成舞臺上的演員。而我們還在大聲抱怨巴厘島為何喪失了淳樸的風情。
旅行的本質是什麼?其實是他者眼光與自我倒影的彼此窺視,是日常文化與異國情調的互相挑逗,也是文化強弱和階級高低的權利關系。只是,本書用戲劇般的場景和精闢的話語輕鬆呈現。
作者簡介:
胡晴舫
她本身就是一個形而上的旅人。出生於台北,臺大外文系畢業後即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就讀戲劇學碩士。1999年移居香港。她一邊各地游走,萍蹤不定,一邊思考女性、現代性、都市等議題,一邊為兩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的媒體專欄提供文化評論。
已經出版的作品包括《旅人》、《她》、《機械時代》、《濫情者》、《辦公室》、《人間喜劇》等。
章節試閱
文化菜色
我坐在新加坡的一家法國餐廳裡;兩天後,又坐進另一家倫敦的印度餐廳。一個星期後;我來到巴黎的一間飯館,看了菜單,才知道他們供應泰國菜。
所以,一天下午,當我在香港中環的一處咖啡店,目睹一位婦人點了一杯熱咖啡和一盤又脆又香的中式炸豆腐,旁邊擺一小碟紅艷艷的辣椒沾醬,當作她的下午茶,我明瞭,自己一點也不應該大驚小怪。
當工業革命開始建造第一條鐵路的時候,信息開始流竄,區域開始互相模仿,人類開始移動,界限開始模糊;飛機緊跟著增快了移動的流通速度,加雜了族群的混合;而電話電報讓整個世界零時差地活在一起。
網路,給了最後的臨門一腳。
我們終於來到一個時代:膚色不再能夠指涉國籍,語言不足以涵蓋區域,服裝無以表達任何身份。
食物,成為最後一種辨識文化的方法。
你沒辦法指著一個黝黑膚色的人類,宣稱他或她是象牙海岸人,你卻可以指著檸檬魚,肯定是一道泰國菜,不用擔憂有人會在你的電子郵箱塞滿抗議信件。
每一個號稱國際大都會的城市,都必須提供一連串不同文化的餐廳名單,泰國菜、巴西窯烤、法國料理、印度口味、中國菜、日本菜……,以證明自己的確是個大熔爐,證明自己擁有豐富「文化」。你居住的城市多「國際化」,端看你有多少食物選擇;你對異質文化的容忍程度有多寬,端賴你對陌生食物的接受態度。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炸豆腐當然可以和著熱咖啡下肚。」我朋友說。沒問題。我收起我愚蠢的表情。
在這個逐漸人工化、幻象化、電子化的超現實環境裡,幾乎所有的有機物或無機物都可以被複製,被移植,被概念化。食物依舊牢牢連接著原始的物質環境,成為唯一真實的現實。
與物質環境緊緊相連接的臍帶,讓食物成為少數仍擁有地區限制的東西。你可以在美國紐約生產製造跟印度加爾各答一模一樣的建築物或瓷器或梳子或釘書機,可是你就是無法種植一模一樣的香料;即使你從印度進口或移植,你還是無法判斷在那種天氣下一個印度廚師究竟會灑下多少種香料,去刺激你的味蕾,讓你開懷大吃。你只能模擬,只能猜測,只能回憶。同理,你能在台北做出全世界最好吃的日本壽司,卻不見得是最道地的口味。
因為,最道地,不一定是最好吃。
透過電子圖像語言,你已經可以和你自己的Ota Benga(註一)直接作朋友,往舊金山觀賞大橋的落日,到米蘭名店購買一條褲子,不必使用你的身體也能經歷一切。但是,要吃一支北京糖葫蘆,活在電子世界的人們依然要返回物質世界,使用自己那碳水化合物做成的肉身,親身咬下一口。
我們的身體就是文化的記憶。我們就是我們吃下去的食物。今後,廚師不叫廚師了。請稱他們作「文化工作者」。
(註一):二十世紀初,被美國人帶回紐約的非洲土著。
疆界
一群人去澳門,搭渡輪回香港。所有人都擁有香港居留權和一張香港身份證,都在一家國際知名的美商金融證券公司工作。到了香港海關,如同電影裡警察抓犯人時亮警徽般神氣,美國公民晃一下護照。不需一秒鐘功夫通過;法國人花費兩秒鐘進關;新加坡人過去了;台灣人也過去了。通關後,大家說說笑笑,準備共進晚餐。那是個輕鬆的星期日夜晚,香港難得有潔淨空氣可以呼吸。忽然,有人發現少了一個同伴。
印度籍同事被擋了下來。海關將他的護照翻來翻去,對著他的香港身份證一看再看,就是不曾抬頭多看這個印度人一眼。印度人無助地站在海關檯前。他擁有一個美國長春藤大學的博士學位,教育程度高於海關人員許多;一年收入五十萬美金,是海關人員一輩子的夢想數字;平時為人比任何一個香港人都善良正直。那,又怎麼樣?
疆界擋住旅人的去路。
太空中看起來水藍色的一個完整地球,實則密密布滿無形的刻度與界線。每一條線後面都是自然力與政治力的成果。
自然力畫出來的疆界神聖不可侵犯,彷彿帶有上帝親手打印的規定。汝不得隨便跨過界線,否則將賠上性命。古代歐洲人謹守戒令,一直到中世紀結束才航出直布羅陀海峽,離開地中海。迄今,西藏人要跨越喜馬拉雅山,仍要請示神諭。
活在現代社會的普通人,則去領事館申請簽證,請示政治力交配下產生的人諭。
沒有什麼比申請簽證的時候更能夠領會到何謂國家主義,以及個人相對渺小的結構位置。
排隊兩個小時,終於輪到我。三秒鐘,駐紐約的英國領事館就把我解決了。「對不起,從歐洲回亞洲時,你不能過境香港。」原因是,「你是台灣人。」事情發生在香港回歸之前。之後,事情只是更複雜。可是,理由都相同,因為我是個「什麼」人,所以我比其它生物都來得可疑,來得危險,來得更不可信任。那是一個未經審判的判決,我沒有權利爭辯、詢問或向對方證明我不是一個他想像中的惡魔。一點機會也沒有。我只是被告知一個既定事實。如果,我不知道地球是圓的,那麼,只是我個人的不幸。
誰決定我的身份?誰讓我在世上那麼多種族國家的芸芸眾生之中脫穎而出?是什麼讓我看起來比英國偏激左派學者或真理教教徒的日本觀光客看起來更像是一名會在紐約帝國大廈放置炸彈的恐怖份子?
旅行證件並不只是一本貼了照片的護照。你的膚色,你的語文,你的國家,你的種族,也包括在你的旅行證件之內。
那些,你的原罪。
原罪無法用三言兩語解釋,也很難光彩地加以論述。這不是一個人道判斷或思想成果,而是一個政治直覺,代表了文明衝突、歷史糾葛、經濟差距和政治利益。無關乎個人對個人,而是個人對國家,國家對國家,乃至文化對文化。原罪採集體形式出現,從不單獨存在。個案差異不在原罪討論的範圍。所以,一個印度人只是一個「印度」人。如此而已。
當冷戰結束,政治正確風潮吹向大和解的時候,原罪成為唯一的疆界。不落實於實體世界的河流或高山,也不再是硬生生的一條緯度線,它在我們的心裡。那是最後的疆界。也是最困難跨越的一條疆界。
杭廷頓認為這條疆界終會是文明的衝突。我卻依然悲觀地看待成窮人與富人之間恆常的拉距,指向人性中為求生存而不得不採取自私態度的永恆黑洞。只要人類一日還有生存資源分配問題,我們就會恐懼,就會自我保護,就會嫉妒,就會害怕,就會憤怒,就會懷疑任何我們不能一眼穿透其意圖的陌生人。
即使敲碎了柏林圍牆、抹去北緯三十八度線、移開台灣海峽,人類總還是有辦法畫出新的疆界,分辨幫助自我生存與威脅自我生存的敵友,漠視與我無關的生命。宗教可以是個藉口,語言也能是個理由,民族、膚色、性別、高矮,或支持的球隊、上過的學較、喜愛的歌手、閱讀品味、消費能力、口香糖牌子,以及你所用的電腦軟體。
那條由人性溝渠形成的疆界,不是申請一個簽證,就能輕易跨過。
語言
語言不通,讓旅行變得美麗。
當置身陌生國度,語言障礙無法跨越,旅人只能與本地人靜靜相對微笑。沈默,不是敵意,卻是衍生善意的最佳氛圍。
失語的靜謐中,羅馬尼亞的貧窮落後,會是賞心悅目的旖旎風光:斑駁失修的牆壁是一幅渾然天成的抽象畫;每天必須步行十公里去取水的老婦成為樸實的美德化身;冬季積雪達兩公尺高,真是有趣的北國景致;表面龜裂的柏油路上出現一頭老牛,不是交通不便,而是視覺驚喜和鄉野趣味。
一旦說起相同語言,溝通,旅人第一手分享了本地人真正的生命情境,包括對方生活的困頓、希望落空的不滿、金錢不足的痛苦,以及個人的政治見解。你失去冷漠的權利,無法繼續隔著距離,塊狀解讀彼此的形象,而被迫進入所有瑣瑣碎碎的細節。於是,羅馬尼亞不再是一個什麼仍懷有歐洲二十世紀前期風味的浪漫國家,不過是一塊窮困失調的土地,上面住著惶然不安的人們。老舊不是風格,卻是貧困;勤儉不是美德,而是不得不為的生活方式;眼前這位看似安貧樂道的老婦人,一開口就淚流不止,訴著共產主義帶給她的苦痛,國家經濟崩潰,子女紛紛移居國外,棄她一人,往往被冬季大雪困於屋內數天,缺水斷電沒瓦斯。
語言的直接衝擊,要求旅人睜開眼睛。從自身的浪漫醒來。
一位旅行經驗豐富的英國旅人說,去除了階級、社會意識、金錢、性別、國籍,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他發現,有時候,跟語言不通的高棉人遠比他的英國同胞來得容易溝通。說相同的語言,不見得適合作朋友;不說相同的語言,往往更快速墜入愛河。
當語言不通的時候,旅人和本地人之間的差異,可以解釋為文化性,非社會性。本地人做出與自己觀念不符合的行為,再憤世嫉俗的旅人都願意容忍,接受對方的特異。而旅人的格格不入,旅人的笨拙,旅人的愚鈍無感,到了異鄉人面前,也視為當然,被安靜寬厚地包容。
剝開了語言,因語言而建立的整套思想體系也隨之移開;人,不設防露出本質,純淨相對。不帶任何社會雜質。真誠友善,且平等相待。
一旦說起相同的語言,所有層層剝去的社會機制重新復位。彼此差異不是成長背景不同,不是價值觀不同,不是宗教信仰不同,而是階級、智識、經濟、族群等社會性的分門別類,而是對方完全是個混蛋。旅人認出本地人的傲慢封閉,本地人嗅出旅人的膚淺幼稚。感到各自在地球上的存在不過是一種資源浪費。如果他們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將天天擦肩而過,永遠也不會說上一句話。因為他們所屬的社會階級不同。
一位法國朋友交了中國女友。他不說她的中文,她不說他的法語。愛情熱烈地進行。女友終於去學了法文,住到巴黎。他與我碰面,喝咖啡時,擔憂地說,自女友開始用法文表達自己,他懷疑她不是他當初愛上的那個人,「我們基本上不說同一種語文,我不能分辨她腦子裡的東西究竟長得怎麼樣。」他提議說中文的我應該和他的女友見面,聊聊天。
「然後?」
「然後,告訴我,如果她是一個法國女人,我們會不會去同一間咖啡廳喝咖啡,讀同一個哲學家的書,選擇同一類型的電影。也就是說,移開了對陌生文化的好奇,我們還會不會對彼此感到興趣。」他不掩飾他身為知識份子的優越感。
「可是,她的文化也是構成她這個人的一部份,如果你欣賞她背後的文化,你也會喜歡這個人。語言,不過是項工具。」
巴黎索本大學哲學系畢業的他完全不同意,「集體文化是一種學科,我如果要研讀,可以透過旅行,經過書本。語言雖只是一種工具,卻是唯一接近個人靈魂的途徑。一個人怎麼說話,如何造句,使用口氣,在在凸顯自身靈魂的輪廓深度。如果人生是一趟旅行,我希望她是我旅途上的伴侶,而不只是我無意間驅車經過的一處異域風景。」他說。
「讓異域時空引發日常系統之外的感官,這不就是旅行的目的嗎?撼動於言語之外的情感深度,這不是愛情嗎?」我說。
他微笑,「我只怕,自己將文化上的驚豔當作是愛情的徵兆。那,無非是一個無知旅人犯下的錯誤。」
偏見
有時候,旅行的成果是發現偏見。
旅人帶著他的偏見趕路,有些舊偏見被印證,成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見。經由旅人的闖入,則影響了沒有離家的人們看待世界的態度-或,另一面的偏見。
凡是牽涉到人的認知,就不免出現偏見。
我坐在南西小鎮往巴黎的火車上,朋友指著前面一對吉普賽男女,肯定他們必是搭霸王車;在日本東京的一家布店,老闆娘禮貌卻冷酷地堅持,任何中國人做的東西比起日本人做的硬是都低一等,譬如絲;東方女人以為法國男人都多情,西方女人以為中國男人都沙文;德國朋友不喜歡我去法國度假,法國朋友討厭我迷戀倫敦;我聽東方人抱怨西方人縱慾且虛無,聞西方人批評東方人虛偽又迷信;痴醉歐洲文化的人對留學美國者如我加以鄙夷,崇拜美國價值者常常不能理解非現代邏輯內的文化。
面對龐大的宇宙,個人渺小的程度,還真不知道該怎麼描寫。而聽說宇宙第一次擴張的直徑不過一英哩的負四十三次方。可是,這不影響一個小小的人類豢養偉大偏見的能力。
偏見不見得通通是負面的。正面的意見可以解釋成善意,卻依然能是個偏見。有時候,我坐在一個人面前,聽到一個句子,是這樣子開頭:「他們(日本人)都是……」或你可以自行填空成英國人錫蘭人巴基斯坦人坦尚尼亞人澳洲人中國人。令我驚異的並不是這個人如何得到這麼深奧的知識,或這個見解多麼洞澈細膩,而是他的斬釘截鐵。
對自己所見所聞的深信不疑。
從旅人狹小有限的個人視界看出去,一件事太容易是有趣的、驚人的、難忘的,卻很難認定是全面的、唯一的、不變的、總體的認識。因為,凡是牽涉到認知,就得問到標準。誰的標準。決定哪種標準為判斷圭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再打一次世界大戰也不能解決。
偏見,和大爆炸起源無關。偏見跟人類自己的小宇宙有關。正因為一個人類個體這麼卑微不重要,需要以巨大到幾近荒謬的傲慢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我必須以我的價值來確認萬物,換言之,萬物唯有經過我的認可而定位。所以,我是萬物的主宰。
也因此,即使偏見不能真正控制世界運轉和所有彗星將要飛去的方向,卻能讓人類天真地活下去。我相信而且理解我所看到的。如此,我將不會被未知所懼怕。
偏見故事的結尾是,從南西往巴黎的火車上,查票員終於一節節車廂驗票到我們跟前。那一對吉普賽男女放下在前面椅背上翹得老高的赤腳,胡亂套上鞋,男人隨手抹一把鼻水,用同一隻手從襯衫口袋拿出兩張票。查票員面無表情完成他的工作。漸漸,窗外林木消失,建築物塞滿視線。
火車進入巴黎市郊時,很多巴黎人跳馬背式地躍過捷運票口。我的朋友滿懷浪漫地說:「瞧!法國人就是這麼自由不拘!」
旅行不是關於認識世界;而是,關於認識自己。透過偏見。
文化菜色我坐在新加坡的一家法國餐廳裡;兩天後,又坐進另一家倫敦的印度餐廳。一個星期後;我來到巴黎的一間飯館,看了菜單,才知道他們供應泰國菜。 所以,一天下午,當我在香港中環的一處咖啡店,目睹一位婦人點了一杯熱咖啡和一盤又脆又香的中式炸豆腐,旁邊擺一小碟紅艷艷的辣椒沾醬,當作她的下午茶,我明瞭,自己一點也不應該大驚小怪。 當工業革命開始建造第一條鐵路的時候,信息開始流竄,區域開始互相模仿,人類開始移動,界限開始模糊;飛機緊跟著增快了移動的流通速度,加雜了族群的混合;而電話電報讓整個世界零時差地活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