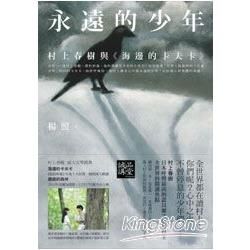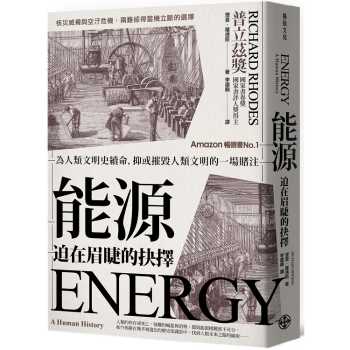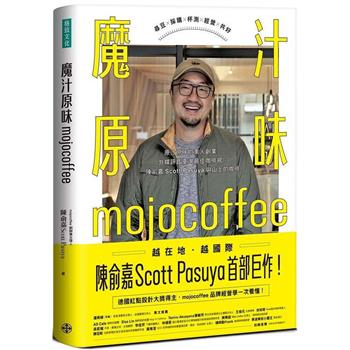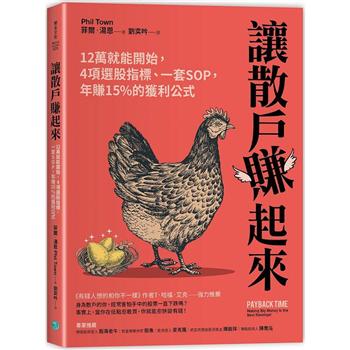作者序
拒絕進入成人領域的「永遠的少年」
──村上春樹創造的奇觀
一、
二十年來,我持續閱讀村上春樹,大概他在台灣出版的中譯本都看了,還有一些原本以為台灣不太可能會有譯本,也就多花一點時間直接讀了日文版。例如他寫音樂的文章,關於爵士樂和古典音樂。
讀村上春樹最大的樂趣,在於書中藏著的各種「下一步做什麼」的暗示、甚至指令。這裡出現一段音樂、那裡出現一本書,於是一邊讀著一邊就想:「嗯,那就去把舒伯特找出來聽聽吧!」或「等我讀完這段就來讀讀《魔山》吧!」
那是一種奇特的閱讀經驗,和平常讀書,專心從第一行讀到最後一行的經驗不太一樣,毋寧比較像是在書中遊逛,逛到這裡會分心想去做點別的事,一面一面的大櫥窗展示著不同的物件,讓你猶豫思考,是要繼續走下去,還是停下來走進這個店家?
而且我清楚知道這種分心,是村上春樹書中本來就內建的邏輯,不是因為我這個讀者特別不認真,也不是因為他這位作者缺乏能力寫出讓人認真讀下去的文字。他的小說,站在這樣的遊逛的基礎上,因而很不一樣。
二、
不過讀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會有特別的困擾。
其中一項困擾,是他的小說在台灣有過那麼多模仿者。尤其是一九九○年代初期,突然冒出來一大堆當時被稱為「新人類小說」的作品,裡面充斥了「贗品村上」。很明顯地,這些作者都讀村上春樹,被他小說中的氣氛、腔調吸引了,所以下筆一寫就寫出這樣的東西。
可是他們的「贗品村上」,也就很容易讓人看破手腳,馬上明白了他們是怎麼讀村上春樹小說的。他們似乎都可以不去注意到村上小說裡藏著的各種暗號、暗示,從來不走進村上小說大街上開設的種種商店,去看看裡面究竟真的擺放了些什麼;他們輕易就被那大街上一種燈光氣氛眩惑了,將櫥窗裡展示的,不管是舒伯特、戴維斯、錢德勒或湯瑪斯曼,都當作只是這氣氛的道具,就這樣走過大街,然後回家在自己的書桌上幻想複製一條那樣的大街。
他們是村上春樹太認真又太草率的讀者。太認真,因為他們很用力地閱讀村上寫出來的文字;太草率,因為他們沒有興趣追究村上鋪陳的各種符號的確切內容。因而他們自己搭蓋出來的大街,如此扁平,像是電視劇裡的拙劣道具布景,街道兩邊的櫥窗都是假的,隨便貼幾張照片,連櫥窗中的物品都不堪細看,當然就更沒有可以供人進入遊逛的店家了。
我極度厭惡這樣沒有景深的小說作品,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寫了文章 批判這種現象,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很多人的印象裡,總以為我是討厭村上春樹的。
三、
不,我沒有討厭村上春樹。比較接近事實的是,村上春樹對我,一直是困惑的謎題。二十年來,吸引著我不斷思考、不斷試圖解題。
《挪威的森林》會是村上春樹最暢銷的小說,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挪威的森林》在日本一上市大賣幾百萬冊,累積至今超過了一千萬冊,卻無可避免在我心中引發了的問題:「為什麼一本如此哀傷的小說,可以在一個逃避哀傷的時代裡,變得如此熱門?」
《挪威的森林》小說一開頭,鋪陳完了飛機上的回憶情景後,立即出現的,是一口井。「井在草原盡頭開始要進入雜木林的分界線上。大地忽然打開直徑一公尺左右的黑暗洞穴,被草巧妙地覆蓋隱藏著。周圍既沒有木柵,也沒有稍微高起的井邊砌石。只有那張開的洞口而已。」
這是真正的開端,也是整部小說的核心隱喻。我們的人生,至少是小說主角們的人生,就是一段走在有著一口隱藏的井的草原上的旅程。他們之所以成為小說的主角,之所以在一起發展他們的愛情故事,因為他們都在無從防備的情況下,掉入了那可怕的井中。
直子形容了掉入井中的可怕:「如果脖子就那樣骨折,很乾脆地死掉到還好,萬一只是扭傷腳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就算在怎麼大聲喊叫也不會有人聽見,也不可能會被別人發現,四下只有蜈蚣或蜘蛛在亂爬,周圍散落著一大堆死在那裡的人的白骨,陰暗而潮濕。而上方光線形成的圓圈簡直像冬天的月亮一樣小小地浮在上面。在那樣的地方孤伶伶地慢慢死去。」
這其實也就是直子自己生命的描述。在她無從防備的情況下,青梅竹馬的情人Kizuki突然自殺了。沒有遺書、沒有解釋,就這樣死了。直子被拋入那大聲喊叫也不會有人聽見的井裡。她僅有能夠得到的一點安慰,是同樣因為Kizuki之死,大受打擊的渡邊君。他們兩個人的愛情,是困守在井底的愛情,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絕望的哀傷。
玲子姊是另一個掉入井裡的人。她比直子幸運又比直子不幸。幸運的是她曾經從井裡被救上去過。她遇到一個單純的人,單純到想和她「共同擁有心中一切」的男人,讓她能夠重新過正常的生活。不幸的是,一次被救上來,無法保證不會第二次再掉下去,又是在無從防備的情況下,玲子栽在一個邪惡的小女孩手中,又掉入那可怕的井裡。
四、
在這樣的核心角色之外,村上春樹又加上了一個冷酷、現實、算計,根本無法或不願體會人間愛情的永澤,和永澤身邊偏偏沒有辦法算計、沒有辦法背叛自己愛情感受的初美姊,兩個人之間無望的糾結。
這些人物構成的關係,為什麼能吸引那麼多人來讀,為什麼他們不會在閱讀過程中,被那深深的哀傷凍傷,至少逼退了繼續閱讀下去的慾望?顯然很多人讀下去,而且還願意口耳相傳鼓吹別人也來讀,這本書才成為一個社會現象,乃至於社會事件。
難道是因為小說中另外一個角色,那個常常瘋瘋癲癲做著大膽行為,講著別人不一定能理解的話的小林綠?只有她,身上沒有沾染那份莫名其妙掉入井中的慌亂、失序與哀涼。
然則,在這樣一群陷入井中掙扎著的人之間,小林綠是什麼?或說,她有什麼力量,不止介入他們的世界,進而改變了這個世界原本的架構呢?
我相信書中有一段話,藏著重要的答案,那是收到玲子姊告知直子狀況惡化的信之後,渡邊在心中對著死去的朋友說的:
「喂!Kizuki,我想。我跟你不一樣,我是決定活下去的,而且決定盡我的能力好好活下去。……為什麼呢?因為我喜歡她(直子),我比她堅強。而且我以後還要更堅強,而且更成熟。要長大成人。因為不能不這樣。我過去曾經想過但願永遠留在十七或十八歲。但現在不這麼想了。我已經不是十幾歲的少年了。我可以感覺到所謂責任這東西。Kizuki你聽好噢,我已經不再是跟你在一起那時候的我了。我已經二十歲了。而且我不得不為了繼續活下去而付出代價。」
「我可以感覺到所謂責任這東西。」這正是看來瘋瘋癲癲的小林綠身上最珍貴的東西。她從來沒有逃避過活著應該要承擔的責任,不管這責任看來多麼不吸引人。她和姊姊兩個人輪流看店、照顧病中的父親。她很累、也很寂寞,會對渡邊說:「我,現在真的累得要命,希望有人在旁邊一面說我可愛或漂亮,一面哄我睡覺。只是這樣而已。」但她沒有逃避,也不是要逃避,「等我醒過來時,就會恢復得精神飽滿,再也不會任性地要求你做這種無理的事了。」
相較於小林綠,小說中的其他角色,都缺乏這份活力、這份勇氣,這份認定並選擇堅強活下去,願意為了活下去而付出代價的精神。這份精神感染了渡邊,應該也就是這份精神撐住了這部哀傷的小說,讓讀者能不絕望地,保持興味地一直閱讀下去吧。
《挪威的森林》結束在這樣一句話上:「我正從不能確定是什麼地方的某個場所正中央繼續呼喚著綠。」
我們誰都不能確定生命走到這一步,究竟是哪裡,沒有把握下一步會不會就掉進那個草原的井裡。我們需要勇氣,我們也就自然地羨幕像小林綠這樣理直氣壯堅決活下去的人。《挪威的森林》寫出了我們的懦弱,以及我們想要呼喚的勇氣對象。
五、
並不是一開始,我就能夠在《挪威的森林》裡清楚讀出這樣的訊息。而是穿越二十年的時間,穿越許多村上春樹的作品,讓我對於小說中的關鍵字愈來愈敏感,也愈來愈有把握。
「我可以感覺到所謂責任這東西。」尤其是活下去的責任,以及對抗命運條件的責任,這是三十年來沒有從村上春樹的小說追求中須臾離開的主題。他在不同的小說中,用不同手法,探索這個主題的不同面向。我們對於自我行為的責任、對於過往記憶的責任、對於依照命令從事的責任、對於幻想、夢想的責任,乃至於對於命運與宿命態度的責任。
最直接、明確展開這項責任主題的小說,是《海邊的卡夫卡》。《海邊的卡夫卡》的小說概念,建立在葉慈(W. B. Yeats)一句詩上:「責任始自夢想。」對村上春樹而言,不是you are what you eat,不是you are what you did,重要的是you are what you think of,甚至是you are what you dream of。你做什麼樣的夢,你懷抱什麼樣的夢想,比其他一切更真實地決定了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而,你就不能只是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必須推前為自己所夢想的負責。
而且唯有願意為自己的夢想負責,人才能勇敢地、強悍地決定自己是誰,是個什麼樣的人。沒有任何一部村上春樹的小說,比《海邊的卡夫卡》更明白、大膽地探索責任這個主題,也沒有任何一部村上春樹的小說,在知識含量上超過《海邊的卡夫卡》。因而在我的私心偏見裡,《海邊的卡夫卡》是村上春樹最好、也最值得耐心遊逛的作品。
二○○八年,我就在「誠品講堂」試著帶領一群學員朋友們,花了五個星期遊逛《海邊的卡夫卡》。除了大家原本輕易可以看到的那條幻化光彩的大街之外,我們繞進一家擺滿希臘神話與悲劇的店舖,一家卡夫卡作品專門店,一家由大江健三郎的文學心靈組構起來,似夢似真的幽微四國森林,以及一家以村上過去小說作品打造的紀念品舖,看看這樣的遊逛能產生什麼樣對於《海邊的卡夫卡》不同的閱讀經驗。
而這本小書,就是以那次五週的課程為基礎,整理增補而成的,後面附加了過去我針對村上其他作品的零星文章。
六、
二十年讀下來,我很確定:村上春樹是個死心眼的小說家。不管他寫什麼樣的小說題材,一旦被他寫了,那小說就帶有濃厚的「成長小說」性質。不過,他寫的,不是少年如何在社會中成長,懂得如何活在社會裡;毋寧是少年如何對抗社會而成長,認知自己的夢想,以及願意為這夢想承擔責任、付出代價。
所以他的小說裡,會一直出現「勇氣」、「強悍」這樣的字眼。在《海邊的卡夫卡》裡,烏鴉如此不容商量地告訴田村卡夫卡:「要做全世界最強悍的十五歲少年。」
這種勇氣、強悍的追求,是成長的關鍵,村上春樹如是堅持,而且堅持:這種勇氣、強悍的追求,是人生唯一最重要的事,至少是小說碰觸人生唯一最重要的主題。
寫了三十年的小說,也就重複寫了三十年少年成長的考驗。即便在最新的大長篇《1Q84》裡,村上春樹寫的,畢竟還是青豆和天吾這兩個人的成長,如何找到足夠的彼此信念,勇敢、強悍地將自己從惡夢中解救出來。那個青豆,當她放棄自殺,決心一定要帶著天吾離開那個惡夢世界時,她身上留著的,也就是和小林綠一樣的血液,就算注定要掉進井裡,都不會輕易解開自己活著的責任。
村上春樹真正創造的奇觀,不是那些幾百萬幾千萬的銷售數字,而是不懈、不停地書寫了三十年成長奮鬥經驗,始終在少年與成人的邊境上徘徊,拒絕正式進入成人的領域,一個執迷於要勇敢、強悍活著的永遠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