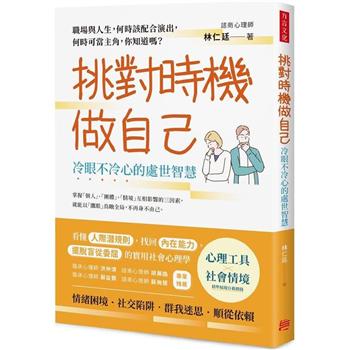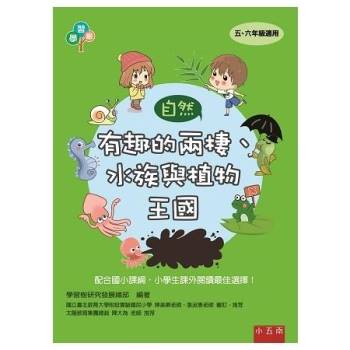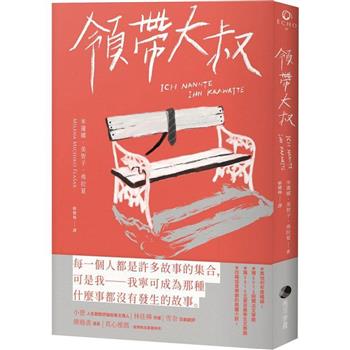許念祖獨自一人站在病房裡。
病房很安靜。
曾經充斥病房的各種冰冷儀器規律聲響都不見了,只剩下偶爾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模糊腳步聲。
他紅腫的眼裡仍泛著淚,默默地看著那張空蕩蕩的病床。
他低下頭,幾滴淚水落在地板上。
然後他抬起頭,深呼吸一口,要自己忍住掉淚的衝動。
在牛仔褲後方口袋的手機發出震動聲,他再次深呼吸一口,這才伸手去拿出手機。
「喂?德叔。嗯,我知道了。」
他聽了一會兒電話。
「爺爺的喪事處理完後,我想去找紀雅清。」
爺爺說,紀雅清會在那棵樹下等他。
*
「唰」的一聲,更衣間的帘子拉了開來。
穿著潔白婚紗的的女子神情愉悅、一臉幸福地端詳著鏡中的自己。
「雅清。」
站在全身鏡前的紀雅清回過神來。
「這件婚紗胸口是不是太低了些?」
「會嗎?」
她重新打量站在鏡子前的自己:整齊盤起的頭髮、尚未施脂粉的乾淨臉龐、耳上那光彩奪目的鑽石耳環。
她看著自己的眼神,原本充滿著終於試到滿意婚紗的喜悅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無奈與妥協。
她的未婚夫不喜歡。
「我覺得不會啊。」她低下了頭,看著自己光潔胸口上的雪白蕾絲抹胸婚紗。
她的未婚夫沒有馬上答話,一身畢挺西裝的男人正聚精會神地看著手裡平板電腦螢幕上的股市行情,微微皺起了好看的眉,而他西裝口袋裡的兩隻手機也兀自響個不停,各種簡訊不斷傳來。
紀雅清看著正忙著賺錢的未婚夫,心情有些複雜。
各種微小的情緒在她心裡交織,獨獨缺了喜悅。
她就要和這個男人結婚了,卻連件自己喜歡的婚紗都不能穿嗎?
眼看男人已經不打算再表示任何意見,紀雅清幾不可聞地輕嘆口氣,揮手招來店員,問:「還有別的款式嗎?」
「小姐,很抱歉,店裡的款式差不多就這些了。不然我們還有些婚紗相片可以先讓您參考一下?或是我們公司也有專業的婚紗設計師可以為客人量身訂製,只是價錢方面自然會比一般婚紗貴了些。不過結婚嘛,一輩子就麼一次,為自己浪漫揮霍一下,也是應該的,您說是吧?」店員一臉燦爛笑容,努力將婚姻的夢幻美麗化作等值的金額推銷給客人。
紀雅清卻只是蠻不經心地「嗯」了一聲,然後說:「那我再看看。」
她走回全身鏡前,轉過身拉上更衣間的帘子,瞬間這個小小的空間裡就只剩下她一個人。
她就只喜歡這件婚紗,這輩子卻是最後一次穿上了。
她的未婚夫像是終於忙到了一個段落,在外頭喊:「雅清,都不滿意的話,那我們就請人設計婚紗怎麼樣?」
紀雅清無聲囁嚅著:「那有都不滿意,我就很滿意這一件啊。」
但儘管有些失落,她還是輕輕回了聲:「好啊」。
*
換下婚紗,離開婚紗公司,紀雅清感覺如釋重負。
她一面匆匆走過馬路,一面從側肩包裡拿出手機,滑開行事曆,然後在「試婚紗」這一欄上打了個勾。
她的眼光往下,見到還有一整排的婚前待辦事項,心情又沈重起來。
結婚怎麼會這麼麻煩呢?
不過就是兩個人以後都要在一起過日子了,卻要大辦婚禮、宴請賓客,於是場地、喜帖、婚紗、攝影等等各種小細節不斷湧來,更是讓她煩上加煩。
煩。
當她決定要與程志遠結婚時,不知為何心裡就常莫名覺得一陣煩悶。
也許是過慣了單身日子,一想到從此以後都要陪伴著另一個人,有些不適應吧?
但她都要三十了呢,恐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遇到像程志遠條件這麼好的對象,一想到這點,紀雅清就要自己趕緊調適心情,不要再因為這些瑣事心煩。
反正總會過去的。
過去之後,就只剩下她和程志遠兩個人了。
但這麼安慰著自己的她,不知為何又有些不安起來。
懷著連自己都難以解釋的複雜情緒,紀雅清走進一間咖啡館,人才走進去,一個穿著俐落套裝的美貌女子便站在櫃台處對她猛招手,然後迎了上來。
「雅清,出狀況了,聽說下個月的專題出了問題,等等就要馬上招開緊急會議。快,先隨便點個東西外帶,我們邊走邊說。」薇薇安說。
「有必要這麼急嗎?」紀雅清被這麼一催,原本想悠閒喝下午茶的心情完全沒了,匆忙到櫃台前點了一杯咖啡。
然後她狐疑地看著微微安手裡的杯子,問:「這是什麼?」
「熱巧克力啊。」薇薇安反問:「怎麼?沒喝過?」
「不是沒喝過。是從來沒見妳喝過。妳今天哪根筋不對?點了這玩意兒?又不是小女生。」
「就說妳觀察仔細嘛。這件事我晚點再告訴妳,先回公司開會吧。」
紀雅清正要掏出錢包付帳,薇薇安突然動作比她更快地掏出信用卡遞給店員,說:「今天我請。」
這下紀雅清更覺得不太對勁了喔。
「怎麼,有求於我?」她問。
薇薇安訕訕地笑了笑,說:「現在只有妳能救我了。」
「用一杯咖啡就想打動我?」
「外加晚上大餐!」眼見紀雅清似乎沒有拒絕的意思,薇薇安又趕緊低聲在她耳邊說:「妳一定要幫我啊,專題出了狀況,要派人出差去重新取材一次,要是妳不去,那就是我去了,但是我現在不能去啊!」
「為什麼不能去?」紀雅清接過咖啡,順從地被薇薇安一把拉住手臂往咖啡館外走。
「我晚上再告訴妳,先去開會救火要緊。」
*
紀雅清與薇薇安回到了雜誌社,匆匆放下手上東西,位置都還沒坐熱,辦公桌上幾疊資料一拿又一起往會議室走了過去。
門一打開,裡頭已經坐了三個人。
坐在最前頭的總編輯一見她們兩人進來,點了點頭,便馬上站起身,毫不浪費時間,說:「原本這次去雲南普洱的專題,是雜誌社下個月的重頭戲。但是我現在一份看得上的文案都沒有,那幾個撰稿人都只是照照相片了事,趕場似的。我不要那些風景照,那些相片網路上隨便找都有,我要的是故事、是真實的體驗,這才是旅行的另一種意義,而不只是走馬看花、拍照留念而已。所以現在這個專題整個推翻重作,必須要去當地重新取材,你們幾個誰能親自去跑一趟?」總編輯說完後,目光緩緩環視在場者。
他的目光首先掃到一個戴著眼鏡的消瘦年輕人,年輕人馬上說:「總編,我現在手裡已經有海岸線旅遊和專欄了,還得和作者開會溝通呢。」
總編輯的目光於是掃到年輕人身旁的女孩,她連忙開口:「之前因為雅清要結婚,我幫她做了一個專題,我現在手上已經有兩個專題,無法再多了。」
「好吧,結婚的人最大。」總編輯說:「那目前就只有薇薇安可以了。」他望向薇薇安。
薇薇安趕忙對紀雅清使了個眼色,紀雅清愣了愣,她完全沒想到薇薇安要她幫的忙,居然是去雲南跑一趟?!她可是要準備結婚的人哪,薇薇安實在是……但眼看薇薇安拼命對她使眼色,使得眼皮都快要抽筋了,她只好先按耐住,轉過頭來對總編輯說:「我去吧。」
總編輯和其他兩位年輕編輯紛紛轉過頭來看著紀雅清,三個人都面露驚訝。
「妳確定嗎?」總編輯問。
紀雅清點了點頭,然後悄悄瞪了薇薇安一眼。
「哎呀,雅清是想趁結婚前來一趟最後的單身旅行嘛。」薇薇安滿臉堆笑打圓場。
其他三個人才這恍然大悟。
多接了一個專案在手的女編輯倒是有些不滿,離開會議室前嘴裡嘟囔著:「結婚了不起嗎?一下說太忙沒辦法做專題,一下子又說要去最後的單身旅行,忙不忙到底是誰決定的啊……」聲音不大不小,剛剛好讓所有的人都能聽見。
紀雅清又瞪了薇薇安一眼,用嘴形無聲地說:「妳最好給我一個好理由!」
*
時間很趕,紀雅清隔天一早就要搭飛機去雲南,下了班之後她就直接回家整理行李,整理得差不多的時候,家裡的電鈴響了起來。
不用猜也知道是誰會這時候過來。
打開門,果然是一臉歉意的薇薇安,手上拎著大包小包的吃食,還有一瓶紅酒。
「這麼多好料的,夠表示我的歉意了吧?」薇薇安走進屋裡,將那些食物與紅酒放在客廳的茶几上,自己坐在沙發上,又說:「先說好,我只負責準備吃的,不負責善後喔。」
「是是是,善後我來做。大小姐,妳是不是忘了我要結婚了?還嫌我要煩心的事情不夠多嗎?這時候還要我跑那麼遠去出差。雲南耶!」
「雲南耶!」薇薇安誇張地學著她的口氣,然後蠻不在乎地甩了甩手,說:「現在坐飛機一下子就到了嘛!」
「到的只是機場,我還要坐上好幾個小時的車程呢!說是要做雲南普洱專題,卻也沒特別指定要走哪些風景名勝,只說要故事、要體驗,時間又有限,普洱不就產茶葉嗎?還能有什麼故事好寫?」紀雅清抱怨著。
薇薇安察覺到她的不對勁,問:「怎麼啦?脾氣這麼大?應該不是因為我請妳救火吧?和婚禮有關嗎?」
紀雅清看了她一眼,大大嘆了口氣,跟著在她身旁坐下。
「他不喜歡我挑的婚紗。」
「為什麼?」
「他說胸部太低了,希望能保守些。」
薇薇安「哼」了一聲,說:「男人都這個樣。巴不得其他女人都穿得曝露些,卻唯有自己的老婆要保守。妳沒跟他說,妳就喜歡那件嗎?」
「這種事情難道還要我說嗎?難道我的表情還不夠明顯嗎?」
「他可能視力不太好吧?」
「薇薇安!」
「好吧好吧,開玩笑而已。」
紀雅清有些失落地又嘆了口氣,身子往後靠在沙發背上。
「我說,妳怎麼一點都沒有準新娘的喜悅?」薇薇安問。
「是很喜悅啊……」紀雅清聲音虛弱,但話才出口,她就覺得這是謊言。
「是該喜悅啊,現在到哪裡去找這麼好的完美老公?工作穩定、薪水高、身材外貌也沒得挑,而且籌備婚禮事事都為妳著想,從婚禮場地到捧花設計,他哪一樣沒陪妳去看去挑去選?」薇薇安說。
但挑的選的都是他自己喜歡的啊。
紀雅清在心裡默默回答。
雖然她也不討厭就是了,但總覺得不該是這樣。
「哎,別說我了。妳不是要告訴我,妳究竟為什麼不能去雲南出差嗎?快從實招來!」
「因為這個。」薇薇安指指自己的小腹。
紀雅清默默地看著好友尚平坦的小腹,很快就明白了原因。
難怪她不喝咖啡了。
「什麼時候知道的?」她訝異地問。
「前天早上。」
「妳想怎麼辦?」
薇薇安難得露出了苦笑,看著紀雅清,說:「還能怎麼辦?」
紀雅清愣住了。
「怎麼可以?」紀雅清輕呼。
「怎麼不可以?」
「德瑞克知道嗎?」
薇薇安搖搖頭。
「妳怎麼不告訴他?說不定他想結婚、想留下孩子呢?」
「小姐,他是我男朋友還是妳男朋友?誰比較了解他?他成天在外頭飛來飛去,我們的關係也沒個準兒,說是男女朋友又不完全是,現在再告訴他有了孩子,他絕對跑得比鬼還快,從此不見蹤影。」
紀雅清有些哀傷地看著薇薇安,躊躇了一會兒,輕輕吐出:「對不起。」
薇薇安「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戳她的臉頰,笑說:「對不起什麼?因為妳找到了好老公、就要結婚了,而我卻還是孤家寡人,還要很可憐地自己去醫院處理這個?」她指指自己的小腹。
「別說了。」紀雅清連忙摀住她的嘴。「妳真的不再考慮嗎?」
「沒什麼好考慮的,早點處理早點好,免得被其他人發現。我已經和醫院都約好了。」
是嗎?
所以才不能去雲南出差啊。
薇薇安其實自己心裡也不太好受,於是想轉移話題,她強打起精神,堆笑說:「妳放心,我會知恩圖報。妳去雲南幫我出差,我在北京幫妳好好調教一下妳的準老公,如何?」
「有什麼好調教的?」紀雅清也跟著她轉移話題,眼光也暫時不再若有似無地往薇薇安的小腹飄過去。
「反正妳聽我的就對了。去了雲南之後,不要乖乖對他報告行蹤,電話也不要主動打,簡訊更不用回,不要一副沒有他就不行的樣子。」
紀雅清微微皺起眉,問:「為什麼?」
「別讓他把妳吃得死死的!偶爾也要讓男人擔心一下,他們才會反省平日是不是太忽略妳的感受。」見紀雅清仍是一副猶豫模樣,她忍不住又說:「總之,妳聽我的準沒錯!」
紀雅清的目光再次落在薇薇安的小腹上,沒有回答。
真的是這樣嗎?
末了,她才輕輕說:「妳沒有喝咖啡。」
薇薇安聽見了。
但她只是「嗯」了一聲,就不再提這件事了。
*
神情憂鬱的年輕人懷裡抱著骨灰罈出現在機場的出境大廳。
許念祖走到航空公司辦理出境手續的櫃台前,櫃台小姐面露為難地問他:「先生,請問這是隨身『行李』嗎?」
許念祖點點頭。
「呃,不好意思,因為其他乘客可能會對您的『行李』感到不舒服,所以能不能麻煩您登機時,將這件『行李』放入背包裡?」
總而言之就是不要讓同飛機的旅客見到有人抱著骨灰罈大方坐飛機。
許念祖深深地看了櫃台小姐一眼,那眼神哀傷得讓她幾乎有些後悔自己失言。
但為了顧及其他旅客感受,她不得不這麼要求。
「要不,用衣服遮掩一下也行。有些旅客對這種事情是比較忌諱的。」穿著航空公司制服的櫃台小姐放輕了聲音說:「許先生,今天班機人比較少,位子沒坐滿,我替您安排在最後一排,左右兩排都沒有人坐。」原本骨灰罈是要另外加購機票的,但反正今天班機沒客滿,她也就睜隻眼閉隻眼算了,別為難人家。
這些年開放兩岸探親之後,是有不少人從台灣這兒帶著老兵的骨灰罈要返鄉安葬,她雖然今天是第一次遇到,但也聽多了這樣的故事。
那麼淺的一彎海峽,因為戰亂,阻斷了多少人的鄉愁,你在這一頭,我在那一頭。運氣好的,好不容易再有音信往來,卻不是天人永隔,就是年華已老去,風燭殘年,不勝唏噓。
許念祖默默領取了機票護照,轉身離去。
櫃台小姐忽然喊了他一聲:「許先生。」
他回過頭。
「這位是……您的親人嗎?」
一般要送骨灰罈回大陸安葬的多半是老兵同袍或親屬家人,不是同樣是老人家,就是已近中年的在台兒女,護照上的名字多半是「台生」。
很少會有這麼年輕的家屬。
而且還是孤孤單單一個人。
就他一人背著個背包、懷裡抱著骨灰罈,不像是在大陸那兒有親人的樣子。
眼身憂傷的年輕人看著她,點了點頭,輕輕說:「他是我爺爺。」
櫃台小姐望著許念祖孤單離去的背影好一會兒,直到他消失在海關入口。
然後她的目光移回面前的電腦螢幕。
許念祖。
目的地:中國,雲南。
念祖。念祖。
一定是他爺爺替他取的名字吧?
他有著一雙令人無法忘懷的眼眸。
而在那雲彩之南的遠方,又是一個怎麼樣的生離死別的悲傷故事?
*
一路奔波,紀雅清從計程車上走下來時,已經是隔天傍晚了。
雲南普洱。
原以為普洱就是產普洱茶的地方,進了城鎮後的確也四處可見片片茶園,但問了司機,才曉得主要產茶地是在附近的思茅、寧洱與西雙版納等地,只因普洱正好是周遭茶葉集散地,自古所有採好的茶都會送到這兒來買賣,因而冠上「普洱」這個名字。
從北京來到位於西南邊疆的雲貴高原,望著遠邊山間悠遠神祕的景色,她想起路上司機告訴她的一段歷史:雲南普洱茶早期曾經由茶馬古道運送至西藏,這古道橫跨窮山惡水,僅能容一人一馬通行,途中還得經過洶湧的瀾滄江,用溜索渡河。
「那馬呢?人可以靠溜索渡江,但馬怎麼辦?」紀雅清當時在車上問。
「一樣靠溜索啊。把馬的四肢綁起來,綁在溜索上,『咻』的一下就送過去啦。」司機笑了。
「那馬多可憐啊?」
馬本來就是膽小的動物,還被這麼折騰,真是身不由己。
「人都過不下去了,誰還在意馬可不可憐呢?」司機有些不以為然。
不過就是用來馱運貨物的動物罷了。
紀雅清不知怎地想起自己的婚禮。
她是不是也是身不由己?
人家說趕鴨子上架,但趕馬上溜索好像也挺生動的。
而她,不過就是背上馱著「婚姻」的馬,一路走呀走呀直到終點為止。
是誰握著她的韁繩?
是她自己?還是她的未婚夫?
她真的願意和那個人共度一生嗎?
她知道「結婚」這個決定是對的,周遭的人也都支持她,但她心底卻有個微小的聲音不是這麼說的。
這就是婚前恐懼症嗎?
哎,不想了,先工作要緊。
她在計程車旁輕輕跺了一下腳。
替她拿行李下車的司機多看了她兩眼。
*
紀雅清拿著行李走進了由老四合宅院改建而成的民宿。
院子的中庭角落躺著一隻黑色的狗,見到她來了,豎起耳朵、抬起頭,警覺地看著她,卻沒有吠叫。
中庭的另外一邊整齊地曬著一排排金黃色的玉米,在夕陽餘暉下閃著微微的光,經過一整天的日頭曝曬,玉米隱隱散發出一股乾燥的陽光氣味。
紀雅清閉上眼,深呼吸一口,心情冷靜了下來。
她拿出相機,拍下那一排排金黃色的玉米,還有那隻又縮回身子打盹的黑狗。
突然間她聽見了輕柔歌聲由遠而近。
燕子雙雙飛……
我和阿哥打鞦韆。
一個穿著拉祜族傳統服飾的少女,身上背著幾乎有她半個身子高的籮筐,腳步輕盈地從老四合宅院的大門前走了過去。
紀雅清連忙跟著她的背影走出了大門。
鞦韆盪到晴空裡,
好像燕子……
女孩的背影走遠了,紀雅清沒有跟上去。
好像什麼?
她抬起頭,想在天際尋找燕子的蹤影。
或是任何鳥兒都好。
彷彿在尋找某種徵兆。
但被夕陽染成橘紅色的天際卻一隻鳥兒都沒有,只有疲倦的、漸染上暗紫色的雲朵在輕輕飄移。
到底是像什麼呢?
紀雅清發現拉祜族女孩已經不見蹤影了。
*
「是紀雅清小姐嗎?」民宿裡的櫃台小姐特地又問了一次。
「是的,我就是。」紀雅清也再次向對方確認。
櫃台小姐交給她房間的鑰匙之後,又彎下腰從地上拿起一個扁平狀的包裹,遞給紀雅清。
「紀雅清小姐,這是您的包裹。」
「我的?」她滿臉狐疑。
誰會寄包裹到這裡給她?
是薇薇安?還是她的未婚夫程志遠?
翻過包裹,寄件地址居然是從台灣來的?
她再仔細看了看收件人的名字,的確是紀雅清沒錯,地址也就是這間民宿。
她狐疑地將包裹翻了翻,感覺一下重量,裡頭似乎是書本的樣子?
她在台灣沒認識什麼人啊,這包裹是不是寄錯了?
難道這裡還有另外一個紀雅清?
但她向櫃台人員確認後,這間民宿目前只有她一個紀雅清。
所以這包裹的確是給她的?
好神祕。
裡面該不會是炸彈什麼的吧?
她再仔細看了看寄件郵戳,是從台灣一個叫做台中的城市寄發出來的,她左看右瞧,被挑起了濃濃的好奇心。
裡頭到底裝的是什麼?
若是有人惡作劇,還特地跑到台灣去寄出這個包裹給她,未免也太大費周章。
儘管知道這包裹的真正收件人可能根本不是她,紀雅清還是收了下來,拿回了房間。
一進房,行李都還來不及打開整理,她便有些迫不急待地拆開了包裹。
總編輯不是說了嗎?要找故事、真實體驗,她現在就是在找題材寫故事呢。
才剛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居然就收到了來自海峽另一邊的神祕包裹,瞧,多有故事性?這麼奇妙的事都能寫成小說開頭了呢。
包裹裡裝的不是書,而是整整齊齊的一疊信,她隨手將那些信在床上攤開,每一封信上的收件人都是「紀雅清」,她數了數,起碼有二、三十封,其中有好幾封蓋著「查無此人」的章,其餘的信封上則是除了收件人的姓名外,一片空白,表示後來這些信都沒有再寄來雲南過,而是用這包裹一次全部寄來。
她隨手抽起最上頭的一封信,發現信封僅是輕輕封上,貼得沒有很牢,她小心翼翼地拆開,但要抽出裡頭的信紙時,猶豫了一下。
這畢竟不是寄給她的東西,隨意翻閱偷看人家的信,好嗎?
寄件人要是知道了,應該會很不高興吧?
可是……可是她真的好好奇啊!
這個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何其多,另外一個叫做「紀雅清」的女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誰寫這麼多信給她?而且看這些信封泛黃的程度,應該至少有十幾年以上歷史了。
而且還是從台灣寄來的。
這情節簡直可以媲美好萊塢那些愛情電影了。
她想起「西雅圖夜未眠」女主角曾說過的一句話:你相信命中註定嗎?
命中註定……命中註定……她看著信封上的字跡,蒼勁的鋼筆字,有稜有角,絕對是男人的筆跡。
她看著陌生男人筆下的自己的名字,心情有些激動與期待。
這會是一個怎麼樣的故事?
於是她不顧一切地將信紙輕輕抽了出來,攤開,上頭的鋼筆字跡已經有些暈染開來,顯示寫信的日子已經有段時間了。
『雅清,時序已入秋,這個地方依舊綠意盎然,沒有幾片枯黃葉子。我病了,我知道自己來日無多,每每在病中閉目,總覺得能聞到熟悉的普洱香氣,但張開眼,病房裡卻根本沒有普洱。也許是我太思念雲南的緣故了。』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回到愛開始的地方:小說.劇本.幕後手記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81 |
藝術設計 |
$ 297 |
影視小說 |
$ 297 |
其他電影 |
$ 297 |
文學作品 |
$ 297 |
電影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回到愛開始的地方:小說.劇本.幕後手記
旅遊作家紀雅清正在和她的未婚夫程志遠在婚紗店試著新裝。他們要結婚了,但是紀雅清並不開心,因為他的未婚夫雖然各個面向都具備了優質老公的條件,但是就是無法了解她的內心。她總是委曲求全,畢竟她認為,也許忽略了小小的自己,就可以換來更幸福的「兩個人」。在一次因緣際會中,她代替好朋友薇薇安來到了雲南,紀雅清遇到了一個男子許念祖,他也正尋找著一個跟紀雅清同名同姓的老婦人,而他的身世彷彿是個深不見底的祕密。
沒想到這一趟旅行,一個台灣來的男子與一名北京來的女子在雲南普洱,短暫七天的交會,竟然改變了兩個人的一生,也讓他們了解了真正的愛情。
本書收錄完整電影劇本 知名女作家Difer精彩的改寫小說
更有導演林孝謙完整電影創作手記精彩大公開
想知道周渝民劉詩詩合作的種種趣事
幕後工作人員如何衡況雲南北京台北打造最清新的愛情電影
楊乃文 黃建為 魏如萱 金曲獎優質男女演唱人如何助陣
完整記錄電影拍攝的點點滴滴 跟著導演經歷最全面的創作歷程
本書特色:
《回到愛開始的地方》(英文:A moment of love),是金穗獎新銳導演林孝謙的電影作品,講述一對來自台北與北京的陌生男女,去雲南追尋一名台灣老人的初戀,學會面對自己感情的故事。
國際知名演員周渝明與劉詩詩主演。
完整收錄電影小說、電影劇本、導演拍攝手記、仔仔與劉詩詩完整訪談,最超值的電影收藏本。
章節試閱
許念祖獨自一人站在病房裡。
病房很安靜。
曾經充斥病房的各種冰冷儀器規律聲響都不見了,只剩下偶爾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模糊腳步聲。
他紅腫的眼裡仍泛著淚,默默地看著那張空蕩蕩的病床。
他低下頭,幾滴淚水落在地板上。
然後他抬起頭,深呼吸一口,要自己忍住掉淚的衝動。
在牛仔褲後方口袋的手機發出震動聲,他再次深呼吸一口,這才伸手去拿出手機。
「喂?德叔。嗯,我知道了。」
他聽了一會兒電話。
「爺爺的喪事處理完後,我想去找紀雅清。」
爺爺說,紀雅清會在那棵樹下等他。
*
「唰」的一聲,更衣間的帘子拉了開...
病房很安靜。
曾經充斥病房的各種冰冷儀器規律聲響都不見了,只剩下偶爾彷彿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模糊腳步聲。
他紅腫的眼裡仍泛著淚,默默地看著那張空蕩蕩的病床。
他低下頭,幾滴淚水落在地板上。
然後他抬起頭,深呼吸一口,要自己忍住掉淚的衝動。
在牛仔褲後方口袋的手機發出震動聲,他再次深呼吸一口,這才伸手去拿出手機。
「喂?德叔。嗯,我知道了。」
他聽了一會兒電話。
「爺爺的喪事處理完後,我想去找紀雅清。」
爺爺說,紀雅清會在那棵樹下等他。
*
「唰」的一聲,更衣間的帘子拉了開...
»看全部
目錄
CH1 電影小說
CH2 電影劇本
CH3 導演手記
CH4 幕後訪問 周渝民、劉詩詩、林孝謙
CH2 電影劇本
CH3 導演手記
CH4 幕後訪問 周渝民、劉詩詩、林孝謙
商品資料
- 作者: 林孝謙、Difer等
- 出版社: 水靈文創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3-08-26 ISBN/ISSN:978986898181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藝術> 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