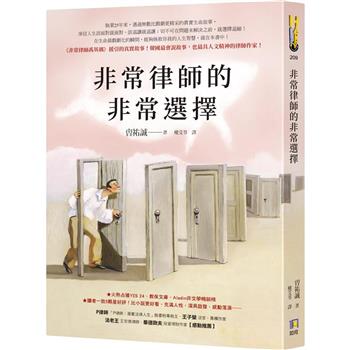「這篇散文是我近來讀到的、最使人傷心的散文;但這傷心裡仍有著歡喜,歡喜我們這個城市竟然擁有這麼厲害的年輕寫手」──作家、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副教授胡燕青
《絢光細瀧》是麥樹堅第三本散文集,收錄十六篇散文。建基於真實體會,〈橫龍街〉、〈屯門河〉串連私人記憶與地方歷史;〈路上的釘〉、〈電子眼睛〉記述生活反思;〈看鯨記〉、〈琉璃珠〉是人生轉折的感悟。
「未幾發現一條湍急山澗,它在色調不一的灌木遮掩下格外韶秀。幾束穿過樹冠的陽光是信使,讓岩石上的水漬、飄升的水氣和脈動的流水閃耀飄忽微光。這種光瞬逝,因而更美,思索良久,我以『絢光細瀧』來形容這條可望而不可即的無名山澗,今天再以此為文集命名。
過去六年有細瀧出谷之感,流動迅猛但絕不磅礴,是現實生活裡沒有大起大落,只是疲累。在頻密的節奏裡,偶有事情值得書寫。」。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絢光細瀧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61 |
中文書 |
$ 261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絢光細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