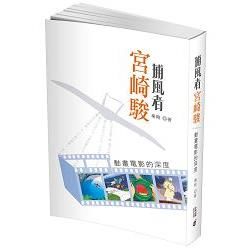★日本漫畫家、評論家大塚英志作序推薦。
★本書以宮崎駿動畫作品為文本作解讀,分析其反戰、親自然、女權主義等觀念,題材吸引。
★本書將開闊的視野與豐富的細節相結合,對宮崎駿導演力圖傳達給觀眾的「訊息」進行了生動細緻的解讀。
★書中穿插近百幅相關圖片,圖文並茂、多元立體地展現出宮崎駿構建的影像世界。
宮崎駿用作品營造出不勝枚舉的奇幻世界:王蟲、腐海、天空之城、龍貓、黑煤球、樹精、麒麟獸、無臉男、波兒……一個個故事中人神共處的世界,是宮崎駿以萬物有靈的視點,對我們所處的自然界存在原理做出的形象化詮釋。而人神共生的世界中,全部生靈與魔法都來自「風」的饋贈。「風動蟲生」,「風化萬物」。宮崎駿卓越的創造力所營造出來的,是一個「風」的世界。
——秦剛
宮崎駿被稱為現代日本的「國民作家」,在世界範圍內享有巨大聲譽。他賦予動畫片這一形式前所未有的表現力,通過動畫片傳達對人類現代文明的憂思、批判和反省。在宮崎駿的動畫片中包含著大量思想元素,如具有東方傳統的泛靈論世界觀、反戰反霸權的獨立情懷、勞動共同體的理念追求與想像、女權主義思想等等。
作者簡介:
秦剛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東京大學日本文學專業博士。編著《感受宮崎駿》《芥川龍之介讀本》,譯著《中國遊記》《河童》《村上春樹論》《日本動畫的力量》等。撰寫日本文學、文化、比較文學等研究領域的學術論文六十餘篇,曾獲得孫平化日本學學術獎勵基金論文一等獎。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吉卜力的作品不僅是關於亞洲和日本的歷史寓言,而且還鞭撻了忘卻歷史的愚蠢和淺陋。秦剛先生研究吉卜力的方法論,是對日本人不肯正視的吉卜力作品的主題進行解讀,以此揭示宮崎駿如何在動畫片創作中努力去踐行對於當下的「返照」。可以說,本書的問世,使得吉卜力作品的深層內涵對日本人而言也是初次得以彰顯。
——日本漫畫家、評論家 大塚英志
名人推薦:吉卜力的作品不僅是關於亞洲和日本的歷史寓言,而且還鞭撻了忘卻歷史的愚蠢和淺陋。秦剛先生研究吉卜力的方法論,是對日本人不肯正視的吉卜力作品的主題進行解讀,以此揭示宮崎駿如何在動畫片創作中努力去踐行對於當下的「返照」。可以說,本書的問世,使得吉卜力作品的深層內涵對日本人而言也是初次得以彰顯。
——日本漫畫家、評論家 大塚英志
章節試閱
總論篇
「捕風者」宮崎駿
本章所要論述的,只有一個問題 —─ 「誰是宮崎駿?」
類似「大師」、「巨匠」一類的桂冠已經因過度氾濫而顯得鄙俗。因此,我試圖從一個新鮮的視角去敘述宮崎駿,而且還要體現出對他的認識和領悟。這樣,我選擇了「捕風」這個關鍵詞。
在我看來,宮崎駿是一個「捕風者」,而且是這個世界上最卓越的「捕風者」,至少在藝術領域是這樣的。所以,也不妨稱他為一名「捕風藝術家」。
以「捕風者」對宮崎駿做介紹和界定,這個想法可能有些過於大膽和出格。因為,在當今的社會體系內,並沒有「捕風」這種職業分工。而且,乍聽起來,「捕風」似乎並非一個褒義詞。在漢語裡,「捕風捉影」常被用於比喻那些沒有事實依據的言行。
然而,這些都不妨礙我將在此做出的論證 ─— 宮崎駿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捕風者」。
「捕風」的動畫製作
一九六三年,宮崎駿從學習院大學畢業後進入東映動畫公司,正式成為一名動畫師,到二○一三年整整五十個年頭。二○一三年九月,他面對海內外兩百多家媒體,正式宣佈今後將退出長篇動畫電影的製作。當然,他表示退出的只是極度耗時、耗力的長篇製作,因為在他看來,自己七十三歲的年紀已經無法勝任長篇製作的巨大工作量。而動畫製作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早已成為他的生存方式,有生之年都不會放棄。宮崎駿是一個為「動畫」藝術而生的人。
關於「動畫」創作屬於怎樣的一種技術性、藝術性的工作,一般說來常見的學院派定義,是「繪畫形式」加「逐格拍攝」。可是,我願意把它說得更為形象和直觀一些。在我看來,「動畫」創作就是用畫筆去「捕風捉影」,在一張白紙上「無中生有」。這樣說不僅直觀,似乎也更能觸及「動畫」的本質。
「動畫」(animated film、animation)一詞的詞源是拉丁語的anima,有氣息、靈魂之意。原始印歐語中的接頭詞an-,即是氣息、風的意思。希臘語中的「風」,就是Áνεμοζ(anemos)。因此,animation 的本意,就是「吹入氣息」、「賦予生命」,使一張張靜止的畫面通過聯結而活動起來,展示動態的自然。而自然界的氣息便是「風」。《莊子.齊物論》中有言:「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大塊噫氣」即自然的呼吸,「風」體現著自然界的存在和奧秘。以展示動感為使命的動畫藝術,其天職就是為靜止之物「賦予生命」,不單是繪形,而且要賦魂。因此,「捕風」重於一切。
在二十世紀獲得全面發展而走向鼎盛的電影藝術,對其本質手法以「捉影」來概括,蓋亦不失精準。能夠捕捉影像的電影,早期在中國即被稱為「影戲」。「捕風捉影」必定曾是人類的千年夢想,只因難於實現,這個詞才成為對無稽之談的比喻。但是,二十世紀的機械技術不僅使之成為可能,而且「捕風捉影」的藝術形式,已經成為現代大眾化綜合藝術的無可爭議的代表。
對「捕風」的玄機,宮崎駿是最有感悟的。他在宣佈引退的記者見面會上,回顧自己在從事動畫行業之初,就覺察到「動畫製作是一件窺探世界奧秘的工作。動畫製作讓你體會到,在風的流動,人的動作、表情、眼神、身體肌肉的運動中,有這個世界的秘密。當我領悟到這一點後,有段時期我感到自己選擇的工作是那樣的深奧,那樣值得去做」。
參觀過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的人,都會看到一個展示動畫片原理的「動起來的房間」裡陳列的電動裝置小窗「我最喜歡走」。在那個木製小窗裡,雲朵、樹木、花草、風車都在風的吹拂下隨風而動,展示著動態。《龍貓》中的次子大步走在這個運動著的世界裡。在這組風景中,還能夠看到一架攝影機。這個電動裝置所用以說明的,就是「風」所帶來的「動態」世界的捕捉,是動畫藝術最本源的動機。
如果上述關於動畫創作的要義在於「捕風」的說法可以成立的話,那麼毫無疑問,作為一名動畫師、即「捕風」之人,宮崎駿所取得的成績是同時代中最優秀的。
日本當代「捕風捉影」的藝術領域的傑出人物,動畫界有手塚治虫,電影界有黑澤明。但獲得了「國民性」認可、同時取得了巨大商業成功的,宮崎駿則是絕無僅有的一位。截至二○一四年,列日本電影票房前六位的電影作品中,只有佔據第四位的是一部真人出演的故事片(《跳躍大搜查綫2 封鎖彩虹橋》,一百七十三點五億日元),其餘五部作品,竟然全部是宮崎駿導演的動畫片。依次為第一位《千與千尋》(三百零四億日元),第二位《哈爾移動城堡》(一百九十六億日元),第三位《幽靈公主》(一百九十三億日元),第五位《崖上的波兒》(一百五十五億日元),第六位《風起了》(一百二十億日元)。
僅就日本國內電影市場而言,在票房收入、觀影人數等數據方面,宮崎駿一個人就戰勝了美國強大的夢工廠荷里活。宮崎駿的作品進入國際影壇創下的一個奇跡,是《千與千尋》榮獲二○○二年第五十二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這是動畫片首次在世界三大國際電影節上摘取最佳電影作品大獎。一年之後,《千與千尋》摘取了第七十五屆奧斯卡最佳動畫長片獎。二○○五年第六十二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將終身成就獎頒發給宮崎駿,宮崎駿由此獲得了任何一個動畫片導演都未曾享有過的國際聲望。
宮崎駿的「捕風」主題
一名動畫作家運用每秒二十四格的畫面,會去捕捉怎樣的一個世界?對於這個根本性問題,宮崎駿的作品具有極大的示範性和啟示意義。
如果說動畫(animated film、animation)以顯現anima(氣息、靈魂)的存在為使命,那麼,宮崎駿是自覺追求動畫藝術本質屬性的動畫人。之所以這樣說,有兩層原因。其一,是他明確表示過,對「靈魂」的顯現和探尋是他永遠不曾改變的動畫主題;其二,他的作品所表達的最基本的世界觀之一,就是天下萬物皆有靈魂的「萬物有靈」論(animism),或稱為「泛神論」的世界認識。再現世界的「氣息」,敬畏一切自然神靈 —─ 這正是宮崎駿動畫片的精神核心。自然界的生命力,通過最普遍的方式讓人感受到其存在的,就是風。風既是自然的呼吸,也是神意的表達。在宮崎駿的世界裡,「捕風」絕不止於一個抽象之說,而是他一以貫之的作品主題。
使他成為日本「國民作家」的首部作品,是一九八四年製作完成的《風之谷》。這部作品的成功,催生了以「熱風」(Ghibli)為名的「吉卜力工作室」,該工作室至今已有整整三十年的歷史。二○一三年宮崎駿推出長篇動畫收山之作《風起了》,也是以「風」為題。宮崎駿和吉卜力工作室的三十年,風雨兼程,「追風」的腳步從未停下。
宮崎駿的動畫作品,為觀影者展示誘人鄉愁的田園般的風景,再現具有厚重歷史感的風物,描摹令人神往的想像空間的風土,刻畫個性鮮明的出場人物的風骨……他的影像世界「風行天下」,無所不包。其作品具有卓絕的畫面表現力,和遠超一般動畫片的質感和厚度。而且,非凡的創造力似乎永無枯竭,每一部新作必定有自我超越,必定展現新的風格、新的風貌。
他用作品營造出不勝枚舉的奇幻世界:王蟲、腐海、天空之城、龍貓、黑煤球、樹精、麒麟獸、無臉男、波兒……這些以畫筆憑虛造像、隨意賦形的現實之外的空想生命,蔚為大觀,自成體系。它們的存在,打通了現實和夢幻的界限,展示出「泛神論」式的、萬物有靈的奇景。因此,在他的作品裡,老屋搬來新主人後黑煤球會悄悄搬家,新搬遷來的一家人會虔敬地向近鄰的大樟樹敬禮,姐姐找不到失蹤的妹妹時會得到貓巴士的幫助,娜烏西卡可以用意念和王蟲交流,飛行石可以托舉起空中墜落的茜黛,阿珊把白狼神視為自己的母親,飛鳥受到來自邪魔神的詛咒,河神在浴場淨身之後會留下砂金表示感謝,五歲男孩會為波兒回到海裡而流淚……一個個故事中人神共處的世界,是宮崎駿以萬物有靈的視點,對我們所處的自然界存在原理做出的形象化詮釋。而人神共生的世界中,全部生靈與魔法都來自「風」的饋贈。「風動蟲生」,「風化萬物」。宮崎駿卓越的創造力所營造出來的,是一個「風」的世界。
描繪了「風」的世界的代表作,當屬《風之谷》。這部如今被認為「改寫了動畫概念」的作品,幾乎是對「風」與「人類」關係的一部系統性闡述。人類建構的龐大的產業文明毀滅千年後,瘴氣污染的世界裡,清風能否再次吹起,讓人類獲得重生?娜烏西卡居住的村落「風之谷」由於海風的吹拂和護佑,免於受釋放瘴氣的腐海的侵蝕,守住了一塊生存的家園。村落裡大大小小的風車不停轉動,是「風之谷」生命延續的象徵。風的吹拂是生存的先決條件,因此,對於一個新生兒的由衷祝願,便是「願他(她)一生有好風相伴」。
宮崎駿說這部影片最大的主題,就是要表現人與自然的關係,為此,必須把「風」和「空氣」的存在,通過動感傳達出來。影片的主人公娜烏西卡,堪稱動畫銀幕上出現的第一個「馭風」者和「呼風」之人。
在《風之谷》片頭的背景畫面裡,宮崎駿獨具匠心地以「風神」形象對娜烏西卡的人物特性做出隱喻性提示。這段掛毯風格的畫面傳達了影片故事背景,概述了「七日之火」毀滅產業文明的「風之谷」前史,並表達出對「風神」重新降臨、為世界帶來新生的期待。
《風之谷》之後的《天空之城》的片頭背景畫面,運用銅版畫風格的動畫,濃縮地再現了人類文明史的演進過程,將「風神」視作潤化萬物之神和推動人類文明演進的原始動力。風神的氣息吹動風車,藉助自然之力的人類,逐漸以機械發明取代自然動力,加大開發自然的腳步,迎來高度發達的機械文明時代,人類發明的各種飛行器開始飛上天空。風車的發明和使用,是人類邁出開發自然的第一步,人類的技術文明由此肇始。在這一意義上,帆船、列車、飛機等一切人類機械的技術發明和應用,都是借用自然之力的「風車」開啟的技術造物實踐的延續。
如是以「捕風」為線索進行論證和考查,我們可以進一步解釋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宮崎駿的作品中,為甚麼「飛行」會成為不可取代的主題,為甚麼他塑造的人物以「擅飛」為特色?
「馭風術」的文明反思
宮崎駿的作品為何多以「飛行」為主題?他塑造的人物為何「擅飛」?對此,不妨通過以下兩點來解釋。其一,是他意欲在自己的作品中導入「風」的視點,從超越地平綫的角度俯瞰自己身處的世界。其二,便是由於宮崎駿對人類古往今來的「馭風之術」抱有超級強烈的興趣。
宮崎駿作品裡刻畫出的「擅飛」之人,從「馭風者」娜烏西卡、魔女琪琪、「紅豬」波爾科到「魔法師」哈爾,他們的「馭風術」從滑翔翼、掃帚到水陸兩用機、魔法的空中行走,可謂千變萬化,千奇百怪。甚至龍貓站在一直旋轉的陀螺上,都能直上雲霄。以旋轉的陀螺作為飛行器,恐怕根本不符合飛行原理,但在宮崎駿式的奇幻世界裡表現出來,就帶有不容爭辯的說服力。出自「紅豬」波爾科之口的一句金言是 ─— 「不會飛的豬,僅僅是一頭豬而已。」儘管他的前僚友告誡他「即便會飛,豬也還是一頭豬」。一頭「會飛」(技藝高超的水陸兩用飛機的駕駛員)的豬的價值,到底是大於一頭豬還是等於一頭豬?這聽起來似乎像一個玩笑式的語言遊戲或無解的悖論,然而,波爾科的那句金言,強調出「馭風」者自身的驕傲,僅此,完全可以入選宮崎駿作品中最令人回味的台詞。對波爾科而言,飛行意味著在一個低俗世界裡保持高昂的理想主義。
如果再舉一例宮崎駿作品中經典而雋永的台詞的話,那麼,這一句出現在《龍貓》的主人公草子和次子的夢境中。姐妹二人在一個月圓之夜,夢到龍貓帶著她們讓剛種下的樹籽瞬間成長為參天巨樹,然後,她們高興地跳到龍貓身上。手撐雨傘、腳踩飛轉陀螺的龍貓,帶著她們在滿月的夜空裡飛馳,草子興奮地對妹妹說:「次子,我們變成了風!」飛行,就是要化身為「風」,與「風」合為一體。宮崎駿在他的奇幻世界裡,為每個人在童年都曾擁有過的變成「風」飛翔的夢想,賦予了充滿童趣和詩意的畫面。
當然,飛行主題的表現,並非總是洋溢著童真與浪漫。對於人類的「馭風術」發展中凝結的技術文明史,宮崎駿持有鮮明的批判態度。他自幼成長於父親和伯父共同經營的飛機製造廠,迷戀各種型號的飛機模型,但對飛機被應用於軍事用途、特別是成為殺戮武器深惡痛絕。《風之谷》、《天空之城》、《飛天紅豬俠》、《哈爾移動城堡》、《風起了》等動畫作品,包括只在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放映過的短片《空想的天空與機械》,展示了從古到今各種虛虛實實的飛行器,而其中不乏淪為戰爭工具的面目猙獰、相貌醜陋的飛行器。只有在遠離戰爭的背景之下,宮崎駿描繪的「飛行」才如天馬行空,酣暢淋漓。騎掃帚飛行的十三歲魔女琪琪的故事(《魔女宅急便》),設定在沒有發生過世界大戰的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歐洲。而年代設定相近,卻以處於「一戰」與「二戰」之間的意大利為舞台的《飛天紅豬俠》,講述的則是主人公逃離戰爭、抵制戰爭的飛行故事。
有史以來流傳最廣、發行量最大的一部世界級童話出自一名飛行員之手,那就是法國作家安托萬.德聖艾修伯里於一九四二年寫成的《小王子》。德聖艾修伯里也是宮崎駿十分喜愛的作家,當一九九八年新潮文庫出版其隨筆集《人類的大地》(Terre des Hommes)時,宮崎駿為該書撰寫了題為《空中的犧牲》的解讀,這篇文章鮮明地體現出宮崎駿的「飛行」史觀。
他在文章的開篇便感歎道:「人類做出的事情過於殘暴。對於二十世紀初剛問世不久的飛行器,人類傾注了才能、野心、勞力、資材,未曾被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而擊退,同時付出了墜落、死亡、破產的代價。這一發明時而受到稱讚、時而備受嘲笑。但是僅僅在十年之後,飛行器便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的主角。」宮崎駿說:「越是愛讀德聖艾修伯里的作品,喜愛與他同時代的飛行員,就越覺得應該冷靜地重新認識飛行器的歷史。對於從羸弱的少年時代就迷上飛機的我來說,那份動機裡包含了未成熟的對於力量和速度的渴求。想到此,我便從飛行器的歷史中,看到了無法用空中的浪漫、征服天空一類的辭藻所掩飾的人類的悲哀。」「飛機的歷史是兇暴的,然而,我卻喜愛讀飛行員的故事。不去辯解其中的理由,那一定是因為我自己的體內有兇暴的東西。」
文中設問:「如果人類至今還沒有征服天空,高空中的雲峰仍然是屬於孩子們心底的憧憬之處,世界又將是一幅怎樣的圖景?製造出飛行器之後,得到的和失去的到底哪個更多?這一點不禁讓人深思。」最後,宮崎駿提議人類在簽署了《全面禁止殺傷人員地雷公約》之後,應該認真思考徹底禁止在戰爭中使用飛行器,他將這個建議稱作「對進步、速度持有懷疑態度,生活在(世界已成為)螞蟻之墳墓時代裡的一隻白蟻的妄想」。
宮崎駿的「妄想」或許在現實中難以立刻實現,但他對人類「馭風術」演進史的洞察和反思,卻是一份重要的精神財富。最新作品《風起了》,正是通過對一名飛機設計師的塑造,揭示裹挾了飛機發展史的戰爭暴力的作品。
在《天空之城》中,依靠「飛行石」懸浮起來的天空之城「拉普達」雖然凝聚了高度的技術文明,卻因背離了「植根大地,與風共存」的古訓,最終只能隕落。當茜黛和栢斯念出讓天空之城毀滅的咒語,所有人力之物轟然傾頹、墜落,只留下巨樹繁茂根系的「拉普達」向太空飄去。這個故事結尾,暗示了走向極致的機械化「馭風術」的末日,具有強烈的文明批判色彩。
總論篇
「捕風者」宮崎駿
本章所要論述的,只有一個問題 —─ 「誰是宮崎駿?」
類似「大師」、「巨匠」一類的桂冠已經因過度氾濫而顯得鄙俗。因此,我試圖從一個新鮮的視角去敘述宮崎駿,而且還要體現出對他的認識和領悟。這樣,我選擇了「捕風」這個關鍵詞。
在我看來,宮崎駿是一個「捕風者」,而且是這個世界上最卓越的「捕風者」,至少在藝術領域是這樣的。所以,也不妨稱他為一名「捕風藝術家」。
以「捕風者」對宮崎駿做介紹和界定,這個想法可能有些過於大膽和出格。因為,在當今的社會體系內,並沒有「捕風」這種職業分工。...
作者序
解讀吉卜力作品中的歷史記憶 ── 秦剛的吉卜力研究方法論
大塚英志
當《風之谷》(一九八四年)這部日後成為吉卜力工作室誕生起點的影片殺青之後,製片人高畑勳對自己也參與製作的這部片子打出了「三十分」的低分,對此他曾經這樣解釋個中理由:
當我接受製片人一職,宣佈開始製作後,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對我而言,我希望這部影片能夠「以巨大的產業文明崩潰一千年之後的未來,來返照現代」,可這部影片未必充分實現了這個目標。(高畑勳《我只是個「外援」製片人》)
作為影片的製片人,高畑勳對宮崎駿的要求是:《風之谷》不僅要描繪出文明崩潰後未來世界的奇幻之景,還必須同時構成對一九八四年「當下」的一種「批評」。高畑勳認為《風之谷》在這一點上,做得並不充分。他還在文章裡談道,他原本期待宮崎駿能通過這部作品「邁入到一個新階段」,結果也未能實現。他所說的「新階段」,也可以理解為對兼具「現實」批判效用的奇境的建構。需要留意的是,上述評論是製片人高畑勳在鈴木敏夫擔任主編的月刊《動畫雜誌》(Animage)上表達出來的意見,完全屬於來自內部的同行者的批評。在吉卜力工作室,宮崎駿身為一名創作者的最大幸運,就是擁有能對他做出尖銳批評的同伴。
高畑勳和鈴木敏夫經常以指出宮崎駿的不足的方式要求他直面歷史和現實。在展示奇幻、表現現實中原本不存在的世界方面,宮崎駿具有無與倫比的才能。但那也往往容易成為「逃避現實」的途徑。宮崎駿之所以對被稱為「御宅族」的動畫愛好者一貫投以尖刻的目光,正是因為他時刻保持警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淪為他們「逃避現實」的工具。而對「御宅族」的不屑,也意味著宮崎駿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高畑勳和鈴木敏夫在參與成為吉卜力起點的《風之谷》的製作時,要求宮崎駿的奇幻世界必須「返照」歷史和現實,這一點十分重要。吉卜力的作品一方面出色地展示了奇幻世界,同時又往往內藏著與歷史和現實的某種隱秘關係,而這種雙重結構,也是來自吉卜力內部的要求。但對於「御宅族」來說,後者恰恰是他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吉卜力的作品對日本的「御宅族」而言,除了被他們認為是純冒險娛樂作品的《天空之城》之外,其他作品未必為他們所歡迎。
高畑勳和鈴木敏夫之所以在宮崎駿作品中尋求高度的批評功能,是因為當邂逅到宮崎駿的傑出才能後,他們意識到終於找到了可以將動畫片提升到藝術高度的可能性 ── 之前的動畫片,是只有在作為面向兒童的商品營銷成功之後,才能夠流行起來。他們之間的相遇決定了此後他們的人生。高畑勳作為製片人和宮崎駿分庭抗禮之後,也通過親自執導《再見螢火蟲》、《柳川堀割物語》、《歲月的童話》等作品,深入思考作品之於現代的意義。對宮崎駿的批評,當然也注定要成為他自己的課題,高畑勳對此是十分認真的。
鈴木敏夫早在《風之谷》時期就是實際上的製片人,這其中重要的事實是他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就「選擇」了宮崎駿。在這方面具有象徵意義的一件事,是一九八一年八月號《動畫雜誌》策劃編輯了「宮崎駿專輯」。《動畫雜誌》原本借勢於一九七八年《宇宙戰艦大和號》的走紅而創刊,繼而通過加大力度編輯在愛好者中備受歡迎的《機動戰士高達》專刊,達到了空前的發行量。一九八一年夏,擔任《宇宙戰艦大和號》角色原案的松本零士原作的《銀河鐵道999》劇場版和《機動戰士高達》劇場版第二部正準備公映,當時正是原作者親自執導動畫片的高潮時期,按說《動畫雜誌》編輯這兩部大作的專輯,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然而鈴木敏夫卻不顧周圍的強烈反對,編輯了當時還不為一般人所知的宮崎駿的專輯。這樣的做法幾乎等於為自己的期刊推動起來的熱浪上澆了一盆冷水,結果雜誌的發行量此後銳減。而這,正是鈴木敏夫「選擇」了宮崎駿、「選擇」了宮崎駿的導師高畑勳的決定性瞬間。
但在這裡卻發生了一個問題。當高畑勳要求宮崎駿的作品具有「返照」現實的批判性,鈴木敏夫將這一批評刊登到自己的雜誌上時,《動畫雜誌》的讀者群體、即八十年代湧現出來的動畫片愛好者(後來被稱為「御宅族」、「新人類」的一代),卻是全然沒有政治意識的一代人。他們根本不會去要求動畫片這種次文化具有批判性。我本人也是戰後出生的第二代,是「御宅族」一代的一員,我們的真實感受是 ── 當年發生在亞洲的戰爭距離自己已經非常遙遠,而且我們還目睹了上一個代際的人(鈴木敏夫屬於這一代際)在政治上遭遇到的挫敗。因此,對《宇宙戰艦大和號》中大和號戰艦被改造成宇宙飛船與影射了納粹的加米拉斯帝國作戰的這種歷史「錯位」,以及那些特攻隊式的自我犧牲的描寫,《風之谷》中超級大國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巨神兵帶到毫無軍事實力的小國等情節,是根本不會過分介意的。
「御宅族」將動畫片作為逃避現實的工具,所以對作品中的歷史寓言,本能地會選擇一個不與政治發生關係的立場全盤拒斥。也可以說,正因為動畫片不「返照」現實,他們才選擇了動畫片作為自己的文化。如今可以輕而易舉地從《宇宙戰艦大和號》中看到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萌芽,從《風之谷》的情節設定中,讀出在日本憲法第九條約束之下的戰後日本在政治抉擇中的糾葛。但是,當時的愛好者拒絕了這樣的闡釋,放棄了政治性、社會性的理解方式,而這日後成為日本受眾對動畫片最普遍的態度。鈴木敏夫之所以選擇了宮崎駿而不是《銀河鐵道999》、《機動戰士高達》,是因為他選擇了蘊含批判性的表現方式,製片人高畑勳同樣在這方面對宮崎駿報以強烈的期待。但一般的愛好者,實際上並非如此。大多數「御宅族」對於宮崎駿的期待,還是身為軍事發燒友的他所描繪出的飛機、成為「萌」文化起源的美少女、為逃避現實提供庇護的奇幻世界。儘管如此,吉卜力卻致力於對「現在」的批評。可以說,發生在創作方與受眾方之間的這種背離,從《風之谷》時期起就初見端倪。
對於《風之谷》,文藝評論家吉本隆明是鮮有的一個例外,他提出了與高畑勳相同的批判。劇場版《風之谷》在娜烏西卡獨自面對大群王蟲終於自我獻身的最後場景中落幕。吉本隆明指出,鑒於這是一部與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的那個「夏季」相連續的「現在」製作出來的電影,這樣的結局實在難以令人信服。吉本隆明要批評的,是影片對於自我犧牲不假思索做出美化的輕率。
吉卜力的作品在《風之谷》以後,一直勇於直面過去的歷史和當下的現實,將其隱含在故事或影像的內部,以寓意化的方式表現出來,以體現出作品對於政治性、歷史性、社會性的追求。但日益擴大的觀眾群體,對此卻拒絕接受。
在這一點上,可以明確地說,吉卜力作品在其基本主旨幾乎未被觀眾接受的狀態下,歷經二十多年終於成為日本的國民化文藝。逃避現實的奇幻世界與歷史、現實的寓意化表現的合二為一是吉卜力作品的共性,而在這樣的雙重結構中,後者幾乎完全被日本的「粉絲」和觀眾所漠視。也就是說,吉卜力一路走來的二十餘年,也正是日本人忘卻歷史的二十餘年。
我與本書作者秦剛先生的初次相會,是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後以日本現代次文化為題舉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那次會上顯而易見的是,對於既包括了天災又引發了核泄漏人禍的那場災難,日本的參會者都沒有將這些本應追究日本責任的重大事態和日本動畫片聯繫起來討論的意識。聽到日本學者列舉《崖上的波兒》裡發生大洪水的段落,藉此一本正經地指出宮崎駿對於災難發生後應急體系之重要有著預見,我感到心情黯淡。在釀成核電事故的根源問題上,日本理應受到更多的問責,而不知為何日本學者卻不去談論,這令我不禁有些忿忿然。
這時,秦剛先生在報告中首先談及戰後日本的漫畫、動畫中反覆講述了核爆記憶,也有很多關於核能和平利用主題的作品,然後他提出質疑,為何從結果上而言日本並沒有能避免核電事故的發生?他的發言給了我強烈的震撼。戰後日本的漫畫、動畫雖然經常以核悲劇為主題,但是從未被讀者所重視,使之成為一種社會倫理。秦剛先生的報告從正面切入,指出了存在於日本動畫愛好者和漫畫受眾中的重大問題。也可以說,他其實是對包括我在內的日本動畫研究者一直以來所迴避的,從歷史、現實的維度去解讀動畫片這一意識的缺失做出了正面批判。他嚴厲的質疑給我留下了深刻的感受。毋庸置疑,從那時起,秦剛先生就成為我最信賴的研究日本動畫的學者。
正如上面這段小插曲所示,秦剛先生對日本動畫的研究,始終堅持了從正面闡釋動畫作品的歷史性、社會性主題和內涵這一基本姿態,而他所面對的問題,又恰恰是被日本學者所躲閃掉的。對於秦剛先生來說,動畫片是一種記載歷史記憶的裝置,因此,他採用的研究方法的特色,就是忠實地細讀作品。他關注作品的每一個細部,同時以充分的資料進行論證,始終努力去把握作品的本質,這種執著的學術態度,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他不僅從吉卜力的作品中解讀出亞洲與日本不可遺忘的共同歷史的寓言,還準確揭示出一個本質性的主題,即不論對於一個單獨的個體還是國家,忘卻歷史就不可能擁有健全的自我認同。
吉卜力的作品不僅是關於亞洲和日本的歷史寓言,而且還鞭撻了忘卻歷史的愚蠢和淺陋。而發自於吉卜力的這一問詰,是足以讓當下的日本人聽起來臉紅耳熱的。秦剛先生研究吉卜力的方法論,是對日本人不肯正視的吉卜力作品的主題進行解讀,以此揭示宮崎駿如何在動畫片創作中努力去踐行對於當下的「返照」。可以說,本書的問世,使得吉卜力作品的深層內涵對日本人而言也是初次得以彰顯。
如何將這些深刻的主題傳遞給未曾充分接納過這些信息的日本影迷?作為日本人,這將成為我的重要課題。為此,在中國能擁有秦剛先生這樣了解日本動畫、既嚴格又認真的一位諍友,我倍感鼓舞。
作為秦剛先生的朋友,我由衷祝福本書的出版!
解讀吉卜力作品中的歷史記憶 ── 秦剛的吉卜力研究方法論
大塚英志
當《風之谷》(一九八四年)這部日後成為吉卜力工作室誕生起點的影片殺青之後,製片人高畑勳對自己也參與製作的這部片子打出了「三十分」的低分,對此他曾經這樣解釋個中理由:
當我接受製片人一職,宣佈開始製作後,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對我而言,我希望這部影片能夠「以巨大的產業文明崩潰一千年之後的未來,來返照現代」,可這部影片未必充分實現了這個目標。(高畑勳《我只是個「外援」製片人》)
作為影片的製片人,高畑勳對宮崎駿的要求是:《風之谷》不僅要描繪...
目錄
序 解讀吉卜力作品中的歷史記憶——秦剛的吉卜力研究方法論 大塚英志
總論篇
「捕風者」宮崎駿
「病疾」隱喻與「母體空間」中的再生
深讀篇
1992《飛天紅豬俠》:紅色寓意與「飛行」、「戰爭」、「女性」、「電影」
2001《千與千尋》:關於「歷史」與「記憶」的國家寓言
2008《崖上的波兒》:異類想像與末世預言
2013《風起了》:「天上大風」時代的向死而生
延展篇
核與現代日本動畫
後記
宮崎駿年表
序 解讀吉卜力作品中的歷史記憶——秦剛的吉卜力研究方法論 大塚英志
總論篇
「捕風者」宮崎駿
「病疾」隱喻與「母體空間」中的再生
深讀篇
1992《飛天紅豬俠》:紅色寓意與「飛行」、「戰爭」、「女性」、「電影」
2001《千與千尋》:關於「歷史」與「記憶」的國家寓言
2008《崖上的波兒》:異類想像與末世預言
2013《風起了》:「天上大風」時代的向死而生
延展篇
核與現代日本動畫
後記
宮崎駿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