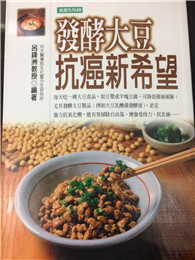徐行之跪得特利索,「噗通」一聲就下去了。
廣府君臉上登時陰雲密布:「誰叫你跪在門口?丟人現眼!」
徐行之「啊了」一聲,整整衣襟爬起來,委屈道:「您沒說進來再跪啊。」
廣府君也不與他贅言,厲聲喝道:「滾進來!」
徐行之在一跪一站之下,辨明這回廣府君是動了真怒了,便不再多話,快步滾了進來。
此次四門出行,為的是捕獲作亂的凶獸九尾蛇,九尾蛇性情凶猛,因此四門首徒皆在其位,帶著師弟立在賞風觀殿前兩側,看樣子是專等徐行之到來。
周北南懷抱長槍,一臉的幸災樂禍,在徐行之目光轉過來時,還特意晃了晃腦袋,口裡嘖嘖有聲。
曲馳沒有周北南那麼輕鬆,他握住拂塵的手指收得很緊,眉眼間盡是擔憂;溫雪塵則手執陰陽環,歷歷循環,藉以活動指腕,從表情上看不出什麼喜怒來。
孟重光與九枝燈均在兩旁侍立,從徐行之進門起目光就雙雙追隨著他,均有隱憂之色。
廣府君身在「離境坐忘」四字匾額下,神情極其冷淡,而這正是他暴怒的表現。
他開門見山地問:「你與何人出去了?」
瞧到這陣仗,徐行之便知道自己再撒謊也沒用了,索性跪下坦蕩道:「卅四。」
「那卅四是何人?你難道不知?」
徐行之抬手摸摸鼻翼側面:「……魔道散修。」
廣府君申斥道:「你與魔道中人修好?徐行之,你當你自己是什麼人?你是風陵山首徒,你同非道中人來往密切,曖昧不明,置風陵山於何地?置清靜君於何地?」
聽廣府君提及師父,徐行之方才分辯道:「師叔,魔道二十年前就已經同四門修好,近些年也少有作亂了。卅四他更是對魔道功法毫無興趣,只專心修習劍術。他既然能修持己心,不肆意為禍,那他和正道之人又有何區別?」
聽了這席話,在場諸人均忍不住將目光轉向九枝燈。
與其說徐行之如此長篇大論,是為著保護卅四,不如說是為了護著在場的某個人。
九枝燈悶聲不語,掌心裡掐著的銅紋吊墜卻已微微變形。
廣府君怒極反笑:「你這是何意?一個魔修,如今竟能和仙門弟子相提並論了?既然如此,你為何不直接棄道從魔?」
此言誅心,徐行之不能再辯,只得垂首:「弟子不敢。」
「不敢?」廣府君冷笑一聲,「世上豈有你徐行之不敢為之事?我若不再施以教訓,你就當真無法無天了!」
他對身旁的徐平生道:「請玄武棍來。」
徐平生微怔,目光在徐行之身上稍稍停留,但也只遲疑了片刻:「……是,師父。」
玄武棍是廣府君的法器之一,純鋼所製,通體銀亮,呈寶塔狀,上生倒鉤銳刺,凡是風陵山弟子,只要聞聽此棍必然色變。
從剛才開始便作壁上觀瞧熱鬧的周北南聽到此令,變了顏色,放下了環抱在胸前的雙臂,訝然道:「廣府君,徐行之的確離經叛道,大錯特錯,可此番又未曾釀出大禍,訓斥一番便算了吧。再者說追捕九尾蛇,他需得出力,望廣府君為大局考慮,暫且寄下這次……」
廣府君冷聲打斷:「此乃我風陵山家事,不需周公子費心。」
周北南語塞,轉頭一個勁兒朝徐行之使眼色,示意他服個軟討個饒,說兩句魔道的壞話便罷了。
徐行之卻不為所動,直挺挺跪在原地,眸光低垂,裝作看不見,氣得周北南直咬牙。
徐平生請來玄武棍之後,廣府君下令:「二十棍。」
徐平生臉色微變:「師父,二十棍是否多了些……」
廣府君看也不看他一眼:「你是何意?願意代他受鞭嗎?」
徐平生立時噤聲,薄唇蠕動片刻方道:「師父,徐師兄輩分高於弟子,弟子不敢下鞭。」
在廣府君沉吟間隙,孟重光與九枝燈幾乎是同時踏步走出:「師叔……」
二人對視一眼,難得在同一時刻找到了共識,齊聲道:「弟子願替師兄受刑。」
廣府君這次是鐵了心要罰徐行之,輕描淡寫道:「三十棍。再有求情,便增至五十棍。」
曲馳見懲罰在所難免,一步跨出,奏請道:「廣府君,晚輩願替您執刑。」
「不必。」廣府君目光轉向溫雪塵,「弟子們既然礙於身分, 不願執刑, 清涼谷溫雪塵, 你可願代勞?」
溫雪塵把玩陰陽環的手指一停,平聲應道:「是。」
接下玄武棍,溫雪塵單手搖著輪椅行至徐行之跟前。與他目光簡單交會過後,溫雪塵道:「將衣服除下吧。」
徐行之掃了他一眼:「不需要。」
溫雪塵:「若是血肉和衣裳黏了起來,到時候吃苦頭的可是你。」
徐行之卻仍是不聽,跪在原地,一言不發。
曲馳臉色不大好,周北南卻稍稍安心了點,還小聲勸慰曲馳道:「雪塵手頭有數,不會……」
話音未落,在場幾人便聽到一聲沉悶的皮肉與棍棒碰擊的悶響。
徐行之立撲在地,天旋地轉之後便是撕心裂肺的劇痛,像是有一萬顆釘子在體內炸裂開來,他一邊顫抖著胳膊試圖爬起,一邊試圖把湧到口邊的血腥咽了下去,但咽了幾口實在是反胃,索性一口全吐了。
溫雪塵又是兩棍連續蓋下,力度與第一棒相差無幾。
就連廣府君都沒料到溫雪塵會下手這麼狠,臉色變了幾變。
周北南目瞪口呆,回過神來後也不顧廣府君還在此處,破口大罵道:「溫雪塵你瘋了吧?你要打死他不成?」
溫雪塵停下手來,持杖安坐,平靜道:「是廣府君要我罰,我不得不罰。」
言罷,他對爬也爬不起來的徐行之下令:「起來。」
九枝燈看著地上那灘血,薄唇微張了幾張,血絲漸漸爬滿雙眼,他抬頭望向廣府君,定定看了片刻,正欲邁步去奪那玄武棍,孟重光便先於他衝出,直接撲跪到了徐行之身上,帶著哭腔喊道:「弟子願替師兄受罰,弟子願……」
「滾回去!」不等廣府君發話,徐行之就沙啞著喉嚨低聲喝道,「誰家孩子啊,有沒有人管?」
孟重光不想會被徐行之呵斥,抬頭慌張地看著徐行之,滿眼都是淚花:「師兄……」
廣府君本想,溫雪塵處事公正,又極厭惡非道之人,想必不會手下留情,卻也斷然沒想到他會下這樣的死手。
然而命令已下,朝令夕改又難免惹人非議,他只得冷冰冰拋下一句話:「繼續罰。三十棍,一棍也不能少。」
言罷,他轉身而去,進了賞風觀主殿。徐平生伴在廣府君身旁,進殿前,他略帶不忍地回首望了一眼,又埋下頭,快步隨廣府君離開了。
廣府君一走,周北南上來就把玄武棍給搶了,他一肚子火,又怕大聲講話會惹得廣府君去而復返,只能壓低聲音對溫雪塵罵道:「溫雪塵,你還真打啊?!」
徐行之這才顫著雙臂直起腰來:「不真打,師叔怎麼會輕易放過我。」言及此,他看向溫雪塵,話鋒一轉:「操你大爺的溫白毛,我知道你下手黑,但就不能輕一點?」
溫雪塵伸腳踢了下他後腰:「話太多了。趴好,裝暈。」
徐行之趴回地上,疼得腦袋一陣陣發暈嘴上還不肯停:「我他媽懷疑你是真想打我。」
溫雪塵平靜地承認:「我是想讓你長點記性。非道殊途之人決不能輕易相與,這點你得記清楚。」
他這麼一承認,徐行之沒脾氣了:「滾滾滾。」
溫雪塵:「……我說過叫你脫衣裳,你也不聽,吃了苦頭算誰的。」
徐行之呸了一聲:「那我是不是還得謝謝你提醒?」
溫雪塵:「不客氣。曲馳,接下來二十七杖你來打。」
曲馳將拂塵交與身旁的師弟,挽袖接過玄武杖:「你放心,我下手有數。不會太疼。」
周北南不樂意了:「還打什麼?一個個這麼實在,腦子都進水了吧?我去跟廣府君說你暈了,就不信他還要把你生生打死不成?」
周圍吵吵雜雜成一片,擾得徐行之頭暈目眩。
在暈眩中他回首望去,只見九枝燈站在不遠處,拳頭握得很緊,孟重光淚眼汪汪地盯著自己,看口形大概是在喚「師兄」。
接著,徐行之眼前便徹底暗了下去。
再醒來時,徐行之發現自己趴在床上,床畔邊開著一扇窗,窗外有一眼小湖,金魚戲遊,斜柏青幽,倒是清淨。
他上身衣服已除,口裡有一股百回丹的清涼味道,該是溫雪塵餵給他的,背上雖仍灼痛不已,但已不是不可忍受。
徐行之勉強爬起身來,摸到屋中的臉盆架邊,轉過背對著銅鏡去照背上的傷口,
這不照不知道,徐行之自己都嚇了一跳。
他背上三道觸目驚心的血痕周邊,有一片片不均勻的破損揭口,一看就是血肉與衣服黏連嚴重,不得已只能強行撕下。
徐行之撐著臉盆架,練習可憐巴巴的表情。
廣府君再如何說也是他的長輩,既是醒了,他也該去找廣府君承認錯誤,免得他覺得自己無禮,把剩下的二十七鞭再給他補齊全了。
徐行之正在練習,突然聽得背後傳來孟重光的聲音:「師兄在做什麼?」
徐行之回頭笑道:「照照鏡子。不過我真是越看越英俊,都挪不開眼了。」
孟重光卻難得沒有被徐行之逗笑,端著銅盤進了門來:「重光給師兄上藥。」
「呵,這麼多藥。」徐行之光著上身走上前,取了一瓶,放在手裡細細端詳,「……這瓶子好認,是清涼谷的。這瓶是丹陽峰的,看這花紋就知道。他們都有心了。」
孟重光咬牙:「打了師兄,還來充好人,這算什麼?」
他看著徐行之那道延伸到肩膀的傷疤,輕聲道:「我真恨不得殺了他們。」
徐行之愕然,抬眼與孟重光視線相碰時,陡然心驚了一瞬。
但很快,那叫徐行之心臟抽緊的目光便被一層盈盈的眼淚軟化下來。
孟重光咬著唇,細聲道:「師兄……」
徐行之立即心軟不已,把剛才孟重光眼中一掠而過的狠厲殺意拋之腦後:「哭什麼,我都沒哭。」
孟重光躲開徐行之的手,帶著軟綿綿的哭腔賭氣道:「……沒哭。」
徐行之伸手抱住孟重光的後頸,哄小貓似的捏了捏:「師兄那時候吼你,生師兄的氣了?」
「我是生師兄的氣。」孟重光臉色煞白,「師兄明明只要說上一句非道之人的不是,廣府君何至於氣惱至此?你分明就是不忍心九枝燈被師叔責罵,你……」
「叫師兄。」徐行之略略皺眉,「九枝燈是你師兄。你這樣連名帶姓叫他,太不像話。」
孟重光心裡本就對九枝燈介懷不已,又聽徐行之這麼說,頓時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目光:「……師兄,你為了他說我不像話?」
徐行之語塞:「我……」
孟重光把藥盤往徐行之懷裡一推,撒腿就跑。
徐行之拔腿追出幾步,到門口才覺出後背疼痛,扶住門框搖搖欲墜時,恰好靠入一人的懷抱中。
孟重光本來就把步子放得很慢,下了門口臺階就不動了,只等徐行之出來,誰料想九枝燈會從半路殺出,將差點摔倒的徐行之攬進了懷裡。
九枝燈臉色也不好看:「師兄,你身上傷得嚴重,我扶你進去。」
徐行之冷汗盈額,半句話也說不出來,被九枝燈環住腰身,送回了房間。
徐行之身上的肌肉練得極漂亮,又薄又結實,腰卻精瘦精瘦,一臂便能環抱過來。
見九枝燈和徐行之摟摟抱抱,動作那般親密,孟重光立時後悔了,往回衝了幾步,卻只能眼睜睜看著門在自己眼前合上。
他氣惱地拍了幾下門,卻發現門上被九枝燈施加了靈力,若非同樣動用靈力是絕打不開的。
而按照常理,孟重光與九枝燈靈力相距甚遠,根本無法破門。
孟重光在門口盤桓幾圈,臉色難看至極。
九枝燈把徐行之抱至床上,安置好後,揭開藥瓶,將藥油倒在手心,又把手往復搓熱,細緻地為他上藥。
徐行之把虛汗遍布的臉頰壓在床上,皺眉忍疼,一言不發。
徐行之既不說話,寡言的九枝燈自然不會多說些什麼,但他顯然是有話想要講,多次欲言又止的模樣看得徐行之都覺得有些好笑了。
他虛軟著聲音道:「小燈,想說什麼儘管說。」
九枝燈忍了又忍,問:「師兄,疼嗎?」
徐行之:「……這不是你想問的。我疼著呢, 你再不問出來, 待會兒我再睡過去, 你可就又問不成了。」
九枝燈呼出一口氣,方才道:「師兄,你這次出去,有幾個知情的?」
徐行之答:「我誰也沒告訴。」
他跟卅四會面,向來是卅四偷跑來找他,他再跟著出去,他瞞都來不及,怎麼會隨便跟人言說。
「就在一個時辰前,廣府君突然召集我們,並問及你的去向。但我看廣府君的模樣,分明是知道你已經去會了卅四。」九枝燈停頓了片刻,才問道,「……師兄可曾想過,是不是有人告了密?」
徐行之久久地沉默著。
當九枝燈幾乎以為他已經睡過去時,他輕鬆地開了口:「嗨,什麼事兒,怎麼可能。」
九枝燈微微皺眉:「師兄……」
「誰敢告我的密?也不怕我把他腦花子打出來。」徐行之輕鬆道,「我就是倒霉催的,別想那麼多。」
九枝燈輕聲說:「既然師兄不想提,我便不提。」
徐行之沉默。
「但師兄心裡要清楚。」九枝燈又道,「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師兄這般真心相待。」
徐行之樂了:「知道知道。你小子倒能訓起我……哎!」
藥油流進傷口, 開始起作用了, 疼得徐行之又是一片冷汗落下來:「要死!溫白毛個王八蛋……嗯──」
他曲起身體來,後背漂亮的肌肉線條一起一伏,攣縮不止,在九枝燈的掌心裡來回蹭動。
要不是九枝燈在身邊,他必然要張口罵到溫雪塵祖宗十八代去。
九枝燈心疼得一頭大汗,向來穩重的聲調也動搖了不少:「師兄……」
他不自覺一遍遍撫摸著徐行之的身體,他腰腹處的肌肉一下下收縮著,本來是男子氣息豐沛、張力韌性極強的畫面,但卻看得九枝燈漸漸面紅耳熱起來。
他的指尖沿著徐行之後背緩緩下滑,落在了那枚銀環蛇印的烙痕上。
過了那麼多年,這個烙痕還是清晰得嚇人,就像是昨日才烙上去似的。
此傷看似平淡無奇,然而九枝燈知道,它要比徐行之身上現在交錯著的幾道血淋淋的創口更嚴重。
可以說,他渾身上下受的最重的傷,莫過於這一個圓形的火紅蛇印。
自從受了這傷,徐行之的功力進益速度便慢了許多。儘管他從不言說,日日過得樂呵呵的,但這處舊傷對他的影響著實不可小覷。
他再不跟要好的幾個師弟一道鳧水玩鬧,也不肯當眾解衣,其實就是不想叫別人發現他這處傷。
九枝燈心中明瞭,當年徐行之若是稟明師父師叔自己身上有傷,定不至於被寒毒侵體,落下病根。
但是,他要是選擇稟告上去,那麼按照清靜君對徐行之的疼寵,就必然會追責下來。
自己本是魔道,身分不乾不淨,又平白給師兄惹來了這樣的麻煩,必會嚴懲不貸,說不定還會被遣返回魔道,繼續過那不人不鬼的日子。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反派他過分美麗(2)(限)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反派他過分美麗(2)(限)
徐行之在自己的話本裡寫道:
在山的那邊海的那邊有一群大反派,他們伶俐又可愛,
他們千奇又百怪,他們勤勤懇懇,要從牢裡逃出來。
後來,他穿進了話本裡。
世界說:你的設定攪亂了世界秩序,你要把打算衝破牢籠、占領世界的反派boss殺掉。
徐行之說:對不起,我只是一條鹹魚。
世界說:沒關係,反派是你親手寵大的師弟,他最聽你的話了。
徐行之:……我沒寫過這樣的設定。
boss溫柔臉:師兄兄,你喜歡這條金鎖鏈,還是這條銀鎖鏈?你慢慢選,我什麼都聽你的。
徐行之:……我真沒寫過這樣的設定。
——這設定,一切如你所願。
作者簡介:
騎鯨南去
知名網路小說作者。
章節試閱
徐行之跪得特利索,「噗通」一聲就下去了。
廣府君臉上登時陰雲密布:「誰叫你跪在門口?丟人現眼!」
徐行之「啊了」一聲,整整衣襟爬起來,委屈道:「您沒說進來再跪啊。」
廣府君也不與他贅言,厲聲喝道:「滾進來!」
徐行之在一跪一站之下,辨明這回廣府君是動了真怒了,便不再多話,快步滾了進來。
此次四門出行,為的是捕獲作亂的凶獸九尾蛇,九尾蛇性情凶猛,因此四門首徒皆在其位,帶著師弟立在賞風觀殿前兩側,看樣子是專等徐行之到來。
周北南懷抱長槍,一臉的幸災樂禍,在徐行之目光轉過來時,還特意晃了晃腦袋,口裡嘖嘖有聲...
廣府君臉上登時陰雲密布:「誰叫你跪在門口?丟人現眼!」
徐行之「啊了」一聲,整整衣襟爬起來,委屈道:「您沒說進來再跪啊。」
廣府君也不與他贅言,厲聲喝道:「滾進來!」
徐行之在一跪一站之下,辨明這回廣府君是動了真怒了,便不再多話,快步滾了進來。
此次四門出行,為的是捕獲作亂的凶獸九尾蛇,九尾蛇性情凶猛,因此四門首徒皆在其位,帶著師弟立在賞風觀殿前兩側,看樣子是專等徐行之到來。
周北南懷抱長槍,一臉的幸災樂禍,在徐行之目光轉過來時,還特意晃了晃腦袋,口裡嘖嘖有聲...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