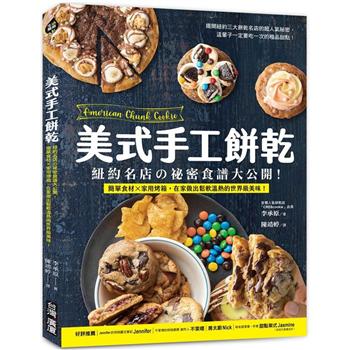本書涵蓋了許多議題,告訴我們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作者將之稱為「愛」──愛他人,載他人生命中帶來影響,讓他人活得更自在。這些事情讓一個人的生命具有高超的價值,整本書值得您收藏,更值得您細細品味的好書。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活出你的價值的圖書 |
 |
活出你的價值 作者:柯許納 / 譯者:俞筱鈞、林淑真 出版社:財團法人基督教橄欖文化事業基金會 出版日期:2004-07-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33 |
二手中文書 |
$ 176 |
中文書 |
$ 176 |
其他宗教 |
$ 180 |
宗教命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活出你的價值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柯許納(Harold S. Kushner)
麻州拿提克市(Natik, Massachusetts)以色列會堂(Temple Israel)的榮譽拉比,這也是他居住的地方。他的著作包括全球暢銷書《好人為何遭殃》(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以及《當怎樣都得不到滿足時》(When All You've Ever Wanted Isn't Enough)。
柯許納的其他著作包括:
《How Good Do We Have to Be? 》
《To Life!》
《Who Needs God?》
《When Children Ask About God》
《Commanded to Live》
目錄
周序周聯華牧師 3
譯者序林淑真傳道 6
作者簡介 9
序 人生的真義 11
前言你很重要 13
第1章 我們活在兩個世界裡 15
第2章 我們如何以退為進? 31
第3章 你渴望成為哪一種人? 49
第4章 野蠻的正義:報復的誘人快感 75
第5章 沙龍(Shalom):追求正直與誠實 103
第6章 家人與朋友:愛讓我們存在 127
第7章 最佳配角 147
第8章 為什麼我們對這個世界舉足輕重? 169
後記 911事件後的世界改變了嗎? 183
譯者序林淑真傳道 6
作者簡介 9
序 人生的真義 11
前言你很重要 13
第1章 我們活在兩個世界裡 15
第2章 我們如何以退為進? 31
第3章 你渴望成為哪一種人? 49
第4章 野蠻的正義:報復的誘人快感 75
第5章 沙龍(Shalom):追求正直與誠實 103
第6章 家人與朋友:愛讓我們存在 127
第7章 最佳配角 147
第8章 為什麼我們對這個世界舉足輕重? 169
後記 911事件後的世界改變了嗎? 183
序
周序
是一本值得推薦的好書。
好書,是因為它深入淺出,以一種不用醞釀的文字,介紹一個深傲而普遍的問題。人內心中良知與成就的衝突是真實的,一個有血有肉、頂天立地的人會遭遇到許多雷同而難以解決的問題。它正像作者另一本扣人心弦的傑作,探討「好人為何遭殃」(原書名:""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一樣的真實。
人生在世都要「活」,活得下去要活,活不下去也要活,但不見得是人人都活得有意義,不見得個個離世的時候都會感到不虛此行。每一個人從早晨一張開眼睛到夜晚入眠時,一直在做大大小小無數次的抉擇,但不見得所做的抉擇個個都合乎他自己的良知。換言之,人的抉擇不一定對別人或對自己的生命有切身的關係,真如古人所說的,有些重於泰山,有些輕如鴻毛。作者在本書中就是要探討這個重要的問題,並且以基督徒的觀點,來幫助人如何使其抉擇對其人生產生重要的意義。
人常是活在兩個世界裡,聽到兩種聲音,甚至活出兩種人來。從聖經中,一直到今天的教會裡,人和人之間常常在見面及分手時,均要互道「沙龍(shalom,平安之意)」。為什麼呢?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人活在世上,怎能沙龍(平安)呢?人之為人都有與生俱來的良知,人之為人都有期待成就的需求。不幸的是,在現實的世界中人卻常誤把權勢、錢財、名譽(儘管人將它當作第二生命)當作成功的記號,卻忘記了人生的真正意義,以致屢屢失去了最重要的「沙龍」。生命要活得有意義,世人的一連串抉擇──如何在良知和成就的衝突中,尋求「沙龍」,是首要的關鍵。
在舊約中,雅各該算是一個「成功」的人了。當初他離鄉背井的時候,光棍一個,什麼也沒有,但他在歸鄉時,卻是「衣錦榮歸」。聖經記載,他送給了他哥哥「消氣」的禮物,就有「母山羊二百隻、公山羊廿隻、母綿羊二百隻、公綿羊廿隻、奶崽子的駱駝卅隻,各帶著崽子、母牛四十隻、公牛十隻、母驢廿匹、驢駒十匹。」
但是我們知道他原是一個行騙高手,按理若有了這些成就,也不能算是他真正的成就。是一直到了雅博渡河口,他與「一個人摔跤」之後,人生才有了改變。本書的作者認為上帝是在「那個時候」與「那個地方」對他有了極大的作為,才有了以後改稱為「以色列」的雅各。而這個與他摔跤的人就是他的良知,雅各必須經過「摔跤」(即內心的搏鬥),才能成為「以色列」,成為上帝的心肝寶貝。
這樣一本深具內容的書,我能為之寫序是我的殊榮,但真正寫序的原因是因為本書是由俞筱鈞博士特別推薦給我的,她自己譯作了其中的大半部,後經由林淑真傳道將之改譯得更為完整,可說是完美的組合。
俞博士自從在美國獲得心理學的哲學博士後,便返國擔任文化大學教授並兼任心理衛生學生輔導中心主任、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所長、訓導長、代校長等。這些職務功在教育,但是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使我為本書寫序的原因在於,她是我七十餘年的老朋友了。我們是小學三、四年級的同班生,從那時候開始,斷斷續續都有來往。而最後的四十年還是我教會的會友。我能為之寫序,誠有榮焉!
周聯華牧師
譯者序
我們就是雅各
一個早春的午後,空氣中帶著一股寒意。用了五、六年的電腦螢幕開始出現跳動畫面,這該是換個新螢幕的好理由,免得急化老花眼的速度。
詢問了價格後, 驅車前往附近一家大型電子量販店,店員在電話中告訴我,大樓地下室有商店專屬停車位,供顧客使用。在擁擠的台北,能有個停車位,是個多麼大的誘惑啊。
賣場位於一棟大樓的地下一樓,大樓管理員要我換停車證後,驅車下停車場,「只能停在B2F喔!」將車子開下坡道,眼前出現一個標示:「B2F」。想都沒想就將車子往前開,裡面的停車場好寬闊,停車格好大,心裡暗自竊喜,對我這種停車技術不高明的人來說,這真是個莫大的福音啊。高高興興的停好車,走到電梯口才發現,這不是B2F,而是B3F,「我將車子停在別人的停車位上了。」
這時我有兩個選擇:回去把車停到B2F,或是賭賭看運氣,反正上班時間,大部份的車位應該都是空的吧?我很想回去重新停車,但手裡抱著13個月大的兒子,重新來過實在麻煩,況且我只要上去拿個液晶螢幕,付錢馬上就走人,前後應該不會超過五分鐘,這樣「暫」停一下應該沒有關係吧?
結果:我沒有把車重新停到正確的停車格,去買螢幕時,因為是打折的開架商品,服務人員很好心的幫我擦拭乾淨,放回原包裝盒,這樣前後大概花了半小時。這30分鐘內,我內心受盡了擔心害怕之苦:「車主回來怎麼辦?」「會不會把我的車拖走?」「我是不是該回去重新停車,等會兒再來取貨?」「應該不會那麼倒楣吧?」心裡閃過千百個念頭,但最後悔的是,沒有在發現錯誤的第一時間,即立刻糾正錯誤。
發生這個小插曲時,我正在翻譯這本書,對本書作者所說內心那兩個善(良知的天使)與惡(邪惡的本性)的聲音的摔跤,有了第一手的經歷。每個人都會犯錯,無心或有心。好人會作壞事。重點不在於我們是否作錯了,而在於我們是否有承認錯誤、改變錯誤,或及時遏止犯罪念頭的能力,好讓良知的天使得勝,讓我們不致一錯再錯,以致無法自拔。
作者以聖經中一個耳熟能詳的故事,雅各與天使的角力,精闢闡述人心裡面善與惡兩股勢力的掙扎。雅各的故事,其實就是我的故事,就是你的故事。
林淑真,寫於西元2004年4月12日
前言
你很重要
對你有信心。我相信你有能力去做偉大的事,一些可以改變這個世界,使之更為美好的事。事實上,或許你已經做了,包括你曾經做過的抉擇、你曾經幫助過的人,這些都有可能發生極大的影響力,重點是,你應該知道這一點。這是我寫本書的理由。
我雖掛名為本書的作者,但事實上它是許多人的心力和努力的成果。我在先前的著作中曾提及我很榮幸有希伯曼(James H. Silberman)作為我的編輯,在這裡我更要說,我相信讀者們也和我一樣為此感到幸運,因為每一頁都有他寶貴的見解和意見。
我也要謝謝席格(Jonathan Segal),感謝他很詳細地審稿,指示出一些重點。
我要再一次感謝我的出版代理商金伯格(Peter Ginsberg),是他促成本書的完成,我為此而深深感謝他。我的妻子蘇蕊(Suzette)在我寫作本書時一直不斷地給我加油,在過程中每當我遇到不順暢時,她都能不斷的容忍我、安慰我。
最後,我願將本書獻給四歲的孫女席拉(Chila)。前兩本著作,我分別獻給她的雙親和她的哥哥,這次該輪到她了。因為排行老二的緣故,她最早學會的幾句話之一就是:「這次該輪到我了。」這句話和本書的主題不謀而合,因為每個人都需要知道我們是重要的,並且這個世界很看重我們。但願本書能夠點出席拉的重要性,以及你們每一個人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