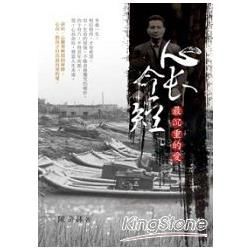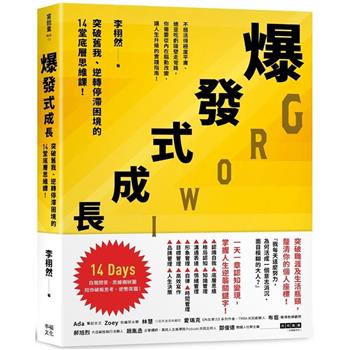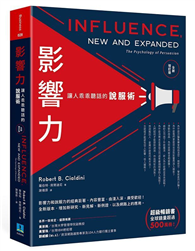推薦序
人間情緣的沉重與輕盈∕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百萬作家 詹明儒
人生不外情緣,文學不外人性。
抽離情緣,人生一無所有,脫離人性,文學形銷骨立。
苦難的時代,總成為文學的最佳搖籃;艱困的生活,總成為人性的嚴苛試煉。
台灣數度歷經改朝換代,百姓飽嘗社會動盪之苦,當權的殖民政府更只著眼於資源取得與勞力壓榨,生民的艱困生活尤為雪上加霜;為了「活著」,情緣與人性,於是絞扭成兩道生命血泉,從時代的石磨隙縫汨汨滲出,滴濺成篇篇血淚文章。
本書雖不具吳濁流、鍾肇政、李喬等前輩,大衝突、大矛盾的大河小說手筆;但其小篇幅、小格局、小故事的「串珠」式的書寫,反而更加足以呈現出另一番小人物、小情志、小理想的文學風貌,而貼近台灣庶民的卑微情愫。
確切而言,這是一本可當做散文閱讀,也可當做小說賞析的農民文學佳作;其內涵擁有類似吳晟詩作的素樸情操,所想要反映的年代則更為提前。
作者世代務農,出生於日本終戰前後,成長於兩蔣治台全期,成就於李登輝當政階段,退休於民進黨首度執政之後;這樣的生命經驗,照理應有極多政治現象的敘述才對,但本書似乎無意於沾染政治色彩,而將書寫重點直指社會底層的窮農困境,委婉地將所遭受的苦難境遇,歸諸於看不見的「命運」。
命運,這種弱勢者無奈持有的宿命觀,於焉如珠串的線索般貫穿本書主旨,同時鋪陳出一則則的血淚故事,串綴成一顆顆的人間珠玉。
台灣有史記載以來,農民一向就是弱勢者的代名詞,身為農家子弟當然最知箇中甘苦;尤其,作者所生長的雲林縣台西鄉的沿海「鹽硝地帶」,地瘠人窮得只能以漁濟農或以農輔漁,百姓生活更須面臨兩面困頓的艱辛。
人生,既然是一種「命運」,各種人間際遇便是一系列的「情緣」糾葛。
夫妻是情緣,父子是情緣,兄弟姐妹是情緣,親戚友朋、左鄰右舍也是情緣。而在人情義理維繫其內的「命運」中,一連串悲歡離合、生老病死的生活過程,於是從而架構出一幅幅或完整或殘缺,或圓滿或缺憾的生命圖像!
命運,一般認為是身處大時代、大環境中,一隻冥冥之手的操控和撥弄;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應該還包含了無數個自己與自己的漫長「拔河」。
本書的這場「拔河」,作者首先藉由老阿嬤的回憶之口,哀怨道出阿公被堂兄弟因細故毆成重傷,不得不舉家遷出祖居地,另謀生路的悲慘往事為啟幕;台西,「海口人」的艱辛歷程,於焉娓娓然形諸文字,刻畫成這支弱勢家族的記憶「年輪」。
阿公是獨子,力薄勢單,這是第一場拔河的最大敗因。所幸,阿嬤生下了多名男丁,命運的巨繩,接手有望。第二名下場者,就是作者身為長子的父親!
接過命運繩索的父親,事事以改善大家庭困境為念,積極於致力家族的振衰起蔽,不僅親自從小長工當到小佃農,從苦勞仔當到日本蔗糖會社的農場「掘頭」;台灣「光復」後,甚至帶領著寡母、妻子和弟弟們幹過私鹽製造,投入「兄弟會」擴大人脈網絡,還參與過台灣民主進程前期的「地方派系」組織,幾乎一切有利於改善家計、振興家聲的任何作法,他都處心積慮、冒險犯難的努力嘗試了。
最後,這位苦心而用心的長子,終於在政府實施「土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下,擁有了一塊被庄民視為「狗屎地」的溪畔旱地,當起所謂的「自耕農」。然而,旱地,必須澆灌更多的心力,才能有所收成。這位一心想當個好農夫的好長子、好兄弟、好丈夫和好父親,竟然在不久後的一場春耕裡永遠缺席了!
永遠缺席的原因是,長期農務操勞及慢性農藥中毒,導致肝暴不治而死。
享年,才只是四十六歲。真可說是「心長命短」,「願望未酬身先死」矣!
是時,甫從軍中退役,猶然少不更事的第三代長子,匆促接過這條拔河長繩。
世途蒼茫裡,父親生前「哪怕做個叫賣雜細花粉的小販」,也不可再種田「過日子」的期望,於是成為作者此後矢志於「人生轉型」的重要目標。
至於,緊緊綁在這條命運繩索上的一家子,四十幾歲的中年寡母、未成年的大妹和二妹,十二歲及六歲的大弟和二弟,還有一個嗷嗷待哺的么妹。如何善後呢?
這似乎需要一些抉擇、一些智慧,更需要更多的諒解、包容和擔待。
所幸,父親臨終時,道出的一句指示:「照兒之心,行兒之意。」
同樣是長子,父親已吃足身為長子之苦。有關身後的沉重擔子,他是希望這個長子能放下就放下,還是期盼這個長兄能承當就承當呢?
父親沒有明說,而作者選擇了後者。「世上最沉重的父愛」之軛,自此挑上了這個第三代長子的肩頭!
沒有猶豫,毫無反顧,理由無他。
這完全是來自短短二十年的與父相處,親炙其「惜緣惜情」的風範之感召。
而叨天之佑,也是蒙父庇護,在隨後二十年裡,作者終於達成這件艱鉅任務。
如本書〈世上最沉重的父愛〉一節所言:「倥傯四十個年頭,家裡早已呈現一名校長、一名代書、一名律師及兩名國小教師,率同諸多子孫承歡於八十五歲高壽寡母膝下的幸福之局」。幸哉此善局,偉哉此壯舉!他這個長子,終於接手英年早逝的父親,拔贏了這場漫漫百年的三代拔河。
對於本書,本序「情緣」之謂,是一種「超越」人類小情小愛的說法。
所要闡釋的是,其實在作者眼中,只要有緣相會者,便是情義相待的對象。
情緣,人間到處都是,而在亂世與逆境下,更是民胞物與,心靈最易感受。
諸如,那輛被父親騎到斷成兩截的老「鐵馬」,那條早年補湊生計的「父河」新虎尾溪,那片阻擋風吹沙卻總被偷採來權充柴火的「保安林」,那頭窮到被他賣掉以「葬父」的老水牛。
也諸如,當年父親被徵調為日本軍伕時,在宜蘭南方澳所巧遇的那位「阿好姨」;戰後被派來本村駐守海防,枕戈待旦以「反攻大陸」的那批中國「青年軍」;作者本身在台中大坑服兵役期間,所真誠相待的那群國軍同袍和街坊友人。
更諸如,作者重建祖厝時所栽植的那片庭樹,所設置的那塊籃球場,退休後所守護的那一批批的社區弟子。
諸多情緣與情義,從童年期的匱乏悲愁,直到青年期的堅忍沉重,直到臨老時的圓融輕盈;終得沈澱成,滿懷「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滿園桃李當看作自己兒孫」的最高澄清心境。
誰敢不說,這對父子、這兩位長子,這種「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偉大」!
謹序於二○一一年教師節 三峽鳶山下
心語一
國家地政士考試及格 執業代書 陳金龍
近日裡,看了大哥新作《心長命短──最沉重的愛》一書,撩起我心裡沉澱已久的糢糊記憶,對父親生前行誼的絲縷牽引,有如浪潮般再度澎湃翻攪不已。
幾天來,我墜入了回顧的深谷,無論歡笑與心酸,任憑點滴回響,在腦海中,一邊咀嚼著字裡行間的懇款細訴,一邊祈盼著阿爸身影如情節般的貼近心窩,更渴望能補捉到父子親情的痕跡。然而,但見痕深情濃,父子情緣偏遭造化作弄,雖摯切卻短暫。
都四十年過去了,想夢見父親的身影,已成一個空白的期盼,一個虛渺的渴望。
那一年,正值寒冬,阿爸走了,我十一歲,已必須學著去領略人世間的生離死別。阿爸彌留之際,掙開含淚乏力的雙眼,叮囑隨侍的家人說兒女中最不放心的是我,要媽媽及大哥特別照顧。
為什麼阿爸最不放心的是我?始終是我心中的疑惑。
跪哭在側,我只知道,從那刻起,再也沒有人白天騎腳踏車載我到田裡摘西瓜,夜晚載我去野溪抓青蛙了。從那刻起,結束了童年,也從那刻起,註定了我早熟的人生。
如今,望著那條野溪,那條水不深卻潺流不斷的新虎尾溪,雖然景觀全變了,而童稚記憶卻仍然依稀如昔。
觸景生情,驀然回首,穿透現在厚厚水泥堤防的掩蓋,回想著那溪邊嫩綠的水草,回想著那堤上密茂的木麻黃;更回想著阿爸忙裡偷閒陪伴子女成長,摘西瓜、抓青蛙的歡樂,是我此生僅存的快樂童趣。
儘管襁褓中,受盡了阿爸無微不至的呵護,但在我的腦海裡,幼兒時期父子相處的溫馨畫面只能僅憑想像揣摩,似有似無,如夢還真,何其糢糊。
父親英年早逝,瞻仰廳壁上業已泛黃的遺像,在看出父親一臉慈藹之餘,卻也更加看出他那人生難以克盡圓滿的無限哀愁。
顯然,阿爸對於沒能完成的世俗凡事,沒能達成的願望,以及來不及看見子女長大的不甘與不捨,是無以名狀的。雖然,平常見到孩子們能奮力勤勉,規矩處事,而聊表寬心,但未能親眼目睹子女的些許成就,這應是父親臨終前最放心不下的牽掛與遺憾吧?
小時候,我沒有兄姊的穩重和乖巧。現在,我終於完全明白了。心長命短,父愛深切,阿爸對我們的願望,就是他此生最沉重的負擔!
寫於二○一一年父親節
心語二
漢昇法律事務所 律師 陳金漢
從小,我就不喜歡父親節。因為,對我而言,「父親」二字,只是從書本裡學來的一個名詞,是我生命中的空白;就連一句罵、一個笑都不曾擁有過的空白,也只像是生活中一個未曾觸摸和體悟過的影子,雖然曾經試圖奮力抓取,偏又總在夢魘中遺落。
渴望、眼淚和傷痛,是我在父親四十餘年陽壽期間,唯一最足以形容的連結。
人生充滿驛站,只一揮手,就成別離;但某些人和事,在來不及揮手前,就已別離。
關於父愛,未及淺嘗即已煙逝,滿懷渴望只能憑藉想像滿足,這是我生命中早已習慣成自然的一份人子哀愁。
對母親而言,父逝是一輩子最深沉的椎心之痛。
四十年來,常聽母親細說著,父親是如何夢裡來,又如何夢裡去的撫慰和失落。從少婦到老嫗,一份掛懷了四十年的情緣和懸念,卻總在夢醒後更加迷茫和落空。
與母親不同,四十年來,任憑如何的殷切祈盼,父親總是不肯入夢;這是我這個身為屘子者,在人生已經走過四十個年頭裡,連一個夢都不曾享有的蒼白和怨懟。
一直以來,對父親的記憶,大都來自長輩口中片段而零散的剪影,生疏得簡直就像在聽聞一個陌生人的故事;若非透過早期屘叔結婚時的團體照,父親對我來說,幾近是個浮水印般的影像,僅略知父叔及祖輩都是在這片土地上與海裡,刨食撈活的辛酸。
然而,四十年以降,所聽聞關於父親的點滴,早已在倥傯歲月下,蒙上厚重塵埃。
雖然,如今早已事業有成,每每思及一再於重要時刻缺席的父親,無不努力地亟想憑靠一張舊照尋找失落中的療慰,也曾經試圖透過生死輪迴或超越時空的思維,探索父親生前死後的狀況。但這都只是「親者欲其生」的迷障,「只有假睡的人叫不醒」,凡俗如我者,何必強求慧根,強求一份自己不到位的渴盼。否則,其又奈何?
日前,接獲大哥新作《心長命短──最沉重的愛》之傳稿,一看書名,早已習慣的那份哀愁,竟又油然撲襲而來,連續糾纏了好幾個莫名失眠之夜。閱讀後才恍悟,凡事,明白就該放下,坦然才能舒泰。
而無形的體現父願,有形的為父寫書,想必是「放下」與「坦泰」的最佳之道了。
世人不免都有生命中的缺口或遺憾。幾十年來,大哥始終傾盡全力兼代父職,彌補弟妹們心中的這份缺口或遺憾,讓我們缺父不缺愛。
如今從國小校長退休後,大哥更透過筆刀忠實刻鏤父子傳承的心路歷程,使得原本單薄模糊的虛像增添血肉,為我們搭起一座精神綿延的虹橋,連綴一段生命長河的缺口,這是對往者的感念,更是對生者的期許。謹諸為誌!
寫於二○一一年父親節
作者序
寫作動機──懵懂與疑惑
痛依舊是痛。血脈相連,血有多濃,情就有多深。任憑歲月的消逝,年歲的增長,那殘缺的傷痕依然烙印著,烙印著……愛恨一線隔,愛深無垠,無垠之愛是至愛。
父親生於日據殖民地時代,曾被徵調當過日本兵,會說幾句日本話。
大概由於這個緣故,影響了我的牙牙學語吧!在我的記憶裡,從小就稱呼阿爸為「阿桑」,阿桑就是「多桑」,就是我的父親。
自從多桑一病不起以後,日子失序,我們全家墜入了生活但求溫飽而不可得的勞碌中。
溫飽,這最基本的生之慾望,對我們家來說,卻是一種奢求。
多桑撒手人世,留下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一堆經年歉收所累積的債務,幾分不適種作的薄田旱地,三對子女和一個無助的寡母。
除了我當兵剛退伍以外,幾個弟妹有的念小學,有的才五、六歲尚未就學,都是幼稚懵懂的年紀。
那個時候,我渴求著一份工作,以貼補家用。
然而,當時以一個高中畢業生而言,要謀求一份工作並不容易。但現實告訴我,找不到工作在家種作那幾分旱地,也是一種工作啊!而且,也讓過慣了鄉間生活的母親有個伴,目前這應該才是安慰喪父傷痛之家的首務吧!
但是,多桑生前一直希望孩子們能多念點書,將來能在公家機關上班,以改變傳統務農看天吃飯的家族命運。因此,這個變故,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瞬間,我有如墜入五里霧中,迷茫無所是從。
然而,長兄如父,我絕對不能驚慌失措。
變故初期,我們總在事倍功半的嘗試錯誤與修正,偶爾親朋的協助,無論是出自於同情,或是對父親生前行誼的念舊,我們都心存感激。畢竟,旁人對寡母孤子之家,好壞都是另眼看待,會有一種近乎矛盾的期待,看著破碎家庭的改變,檢驗著你孤獨的成長。所以,我絕不能等著別人救助,更不能就此倒下!
典型在夙昔。但不見得只有偉人才足以留下典範,平凡人的不平凡作為,往往可以更加貼近這個平凡的市井人間。
因此,多桑「照兒之心,行兒之意」的臨終遺訓,就如此成為我長相左右的座右銘。
多少年來,我們在艱難下打拼,在困境裡攜手扶持,於今容有些許所謂的「成就」,這都是多桑生前留下的風範,所以致之。
在生活中,大弟經常撩起一些童年似懂非懂的片斷記憶:「小四那年,正值寒冬,阿爸走了,我才十一歲,已必須去領略人世間的生離死別。阿爸彌留之際,掙開含淚乏力的雙眼,叮囑隨侍的家人,兒女中最不放心的就是我,要媽媽及大哥特別照顧……」
大弟說到傷心處,每每停頓,若有所思。
「我知道,從那刻起,再也沒有人會騎腳踏車載我到田裡摘西瓜,載我去野溪抓青蛙了。從那刻起,我的童年提前結束了,也從那刻起,我早熟的人生也提前註定了……」
更有時候,他滿腦子疑惑不解,心中總有好多好多的問號:
「為何阿爸臨終前最掛記,最不放心的是我?我只是愛耍小聰明再加上一點頑皮而已,為何是我而不是姐姐或大哥?為何不是那個蠢得只會認些字、背些詩的弟弟,或是剛學會說一點話的妹妹?為什麼啊?……」
直到現在,或許大弟依然不甚理解,多桑臨終為何如此叮囑母親與我的真義。
至於二弟,當時才五、六歲,他對父親的印象更是糢糊。
他多次在著作裡回憶著:「四十年前某一天,父親突然過世,是我上小學前一年,妹妹更小,依稀記得媽媽、哥哥、姐姐和一群人在哭,忙進忙出的。爸爸為什麼睡在大廳旁?死是什麼?死和睡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爸爸睡著了,大家還哭著吵他?我和妹妹只是靜默的站在一旁張望著。從那時起媽媽和哥哥、姐姐,背負了一輩子的椎心之痛,我和妹妹不懂死也不懂痛,記憶中沒有父親的影子,話題中也沒有父親的元素,但這也註定了後來我們還是要痛一輩子……」
二弟在成長的過程中,無論求學與做事,在生活言談裡,經常伴隨著失去父愛的無形傷痛;但對父親僅有糢糊得不能再糢糊的印象,卻徒然只能憑空想像與感懷。
四十餘年來,痕淺痛深。
二弟常用這樣的想法,嘗試著自我平衡,自己療傷止痛:「父親早走,是因為上帝的天堂裡,急缺一個最勤勉的長工。」
但是,痛依舊是痛。血脈相連,血有多濃,情有多長,痛就有多深。任憑歲月的消逝,年歲的增長,那殘缺的傷痕依然烙印著,烙印著……
所以,二弟一直覺得:「失怙,是痛,一種連一個微笑都不太記憶的痛,一種直到懂事後才領略和纏繞的至痛。然而,痛的不是失去,而是痛在虛無中的摸索與渴望。但,任憑渴望再渴望,父親不曾走入夢裡來,父愛只能在冰冷的想像中模擬。很多時候對我而言,父親只不過是個有著血緣關係的陌生人,一個渴望深擁的陌生人。」
「父親,您怎可生不為伴,死不相佑,讓母親獨苦二十年後,還要面對生死不若的殘年,今夜就回來吧!回來看看母親的醜態與殘樣,看看大女兒一夜無聲的啜泣,也看看我渴望與憤怒的眼神。」
「辜負,是的,看見母親四十年孤寂艱辛的歲月,任憑父親走時有著萬般不捨和無奈,我還是如此認為。至少,父親欠母親一個夢中的道歉,也欠我們兄弟姊妹一個夢中的擁抱。經常聽母親細說著:父親是如何的夢裡來,又如何的夢裡去的寬慰與失落。然而,四十年來,任憑我曾經無數次的渴望再渴望,我未曾看見父親走入我夢中,也許是怕我責問,或怨懟得太深,也許是怕我抱得太緊,也許是怕我夢中相見,但夢醒又如何!」(附註:二弟的話引用自《兩滴刺青──母親與我》)
在寫作的字裡行間,在言談中,在在的理解到兄弟倆缺乏父愛的失落,以及父親早逝,在其童稚的歲月裡,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印象裡始終捕捉不到父親的影跡,徒生對父親生平的疑惑與不解。
的確,渴望父愛已是奢求。
在成長的過程中,雖有母親辛苦的呵護,兄弟間的扶持共渡,然在親情的國度裡,總是缺少了一個角,一個無以彌補替代的角。因為,父親如山,阿爸是孩子永遠的靠山。
父喪,大弟國校四年級,二弟才六歲。
懵懂的年紀,不懂生與死的稚幼年歲。當然,可能只記得在一個簡單的喪禮祭拜儀式中「拿香跟拜」,對父親的印象不只糢糊,甚至了無記憶。
因此,都四十年過去了,在其生命中,很難感覺出曾經擁有的父愛至情,曾多少次因感傷而嚎啕大哭過,因挫折無依而傷心過,因不解而怨懟過,因不如意而恨懣過,因……唉!凡生活周遭任何不能與幸福人家比評的事,都怨在缺乏的這一份父愛。只因為,父親早逝。
我是長子,在父親的呵護下成長。父逝那一年,我二十五歲。
在二十五年歲月裡,我看見了父親的勤勉愛家,看見了多桑在大家庭裡肩負重擔的辛勞,更感受到我們的父子情深。
但,父親命薄,父子緣淺。
命薄早逝,也許只能委諸於命運,緣淺情深卻值得終生記取。
畢竟,血脈相連不可抹滅,二十五年為父,即是永世為父啊。
回想臺灣光復後,子姪輩陸續出生,我們逐漸形成大家庭,食指浩繁的生活更吃緊了;父親也是家中長子,他的角色逐漸變得更吃重了。
自從懂事以來,總覺得無論颳風下雨,多桑總是不畏艱險,排除萬難的一手撐持擔當著,冗冗碌碌,期使整個家庭能夠過得起碼的溫飽,期使孩子們可以過得更好。
在清晰的記憶裡,每遇到荒年歉收缺糧,我看見多桑騎著那輛老舊的「二八仔」腳踏車,到處張羅賒欠借糧的情形,看他那碩壯的身軀踩壓著那輛骨架鏽蝕不堪的腳踏車,真耽心著會被壓垮呢!或許有了這個不協調的搭配,更顯得他那堅毅渡日的勇氣,燃點了全家生活的希望,也或許有了這種擔當與堅持,使父親更能在冗碌中扮演起「長兄如父」的角色。
因為,阿公也像父親一樣,極為早逝。
四、五○年代農村的艱辛困苦,在我們家前後兩代都看見了。
為了家,為了兄弟,為了妻小,為了生活上起碼的溫飽,自從阿公被人欺凌以亂棍打成重傷一病不起後,就注定多桑冗碌打拼的人生。
父親年少時,曾當過「苦勞仔」長工,當過糖廠採收甘蔗的「掘頭」。及長,旋被徵召當了「日本兵」,準備赴南洋當軍伕,幸逢「太平」光復,退役後沿襲父祖輩當了好久的佃農,過著由地主發落剝削的日子。
好不容易,在新虎尾溪北岸,以權利買賣的方式承租了一片高亢的沙崙地,喜見由佃農變為自耕農,本以為從此可以去苦離貧,然辛勤耕作偏逢天災飢荒,所幸有了土地便擁有了種作的自主性。因此,只要符合節令的作物,無論雜糧、短期蔬菜、瓜果都種,一家人的溫飽稍見有譜,我們家難得的似有了破繭而出的興奮喜悅。
平凡人的不平凡,總蘊涵著身世的坎坷,有著多少辛酸不為人道者,只有最親近的人方可瞭解個中況味。
多桑在那個年代裡,在其腳踏實地卻似逐夢的生命中,或立下願望、或真心期待、或追求理想也罷!除了阿嬤、母親外,我想單憑任何個人所揣思想像的父親行誼,都是片斷而無以淋漓盡致。
然而,阿嬤在父逝的翌年也跟著走了,母親現在又已八十五高齡。今憑其老人家想當年嫁入寒門,結縭共組家庭一齊打拼的事實陳述,以及我在父親的多方苦心栽培下,朝夕相處所瞭解的點點滴滴,對多桑一生慘澹經營,對兄弟的相攜扶持,對子女的關懷與期待,以及在為人處事上的所見所聞寫成本書,期能加以翔實呈現與紀錄,聊表我這身為長孫、長子者的感懷寸心。
四十有六,不得其年而逝,父親當然是願望未酬身先死的。
多桑何嘗不想長命百歲,而能多所陪伴呵護子女,能看見子女成材成器,能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但無奈造化弄人,心長命短!
失怙是痛,是人間至痛。
至於弟弟、妹妹們對多桑的茫然疑惑,多年來,我曾設身處地的深思過。如果當時我一樣的才小四,一樣的才五、六歲,我必然也是一樣的迷惑啊!
父親的身影,容或在家族成員裡,各有不同的投射。
然而,無論如何,父親仍舊是我心目中永遠的靠山。
陳金鉌 謹識
寫於二○一一年 父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