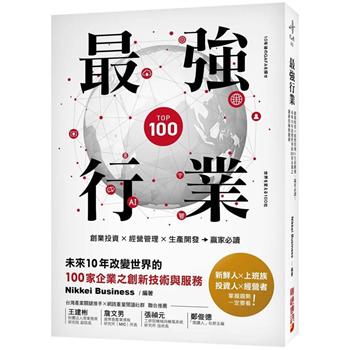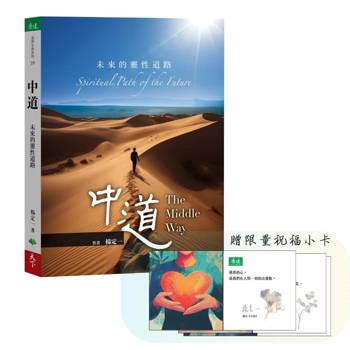我們活著。哪怕末日再靠近,我們也悲哀地活著。
「那一天」就要到來,但我們不會只是等待。
即使再努力也終將消滅,也不曾放棄。
只希望微小的、平凡的自己可以被「記得」;
只期盼在久遠的未來,有人會想起我們;
述說著我們的故事,說「好久好久以前,我認識一個人……」
七個迎接末日的故事,七段平凡又美麗的傳說。
2004年起,年年問鼎日本重要文學獎項,
三浦紫苑,二十多歲即獲得直木賞肯定,驚艷全日本,
作品領域跨越推理、溫馨勵志、輕小說、純文學……全才型新生代女作家!
末日到來前,他們不奢求留下美好回憶,只希望能被「記住」就好
某年某月某日,政府發布三個月後,隕石即將撞擊地球。
唯有「被選中的人」才能搭乘火箭,前往政府布置妥當的火星居住。
日本民眾得知新聞,全國陷入瘋狂;各地暴動不斷,全面失序。
此時,高中生桃子跟朋友決定大幹一場,為女友宇田展開一場瘋狂的鑽石偷竊行動——
宇田的母親吞下那顆鑽石自殺,父親卻在剖開母親的身體、取出鑽石之後,轉送給情婦……
表面上看來,這場粗糙又誇張的犯罪是不良高中生桃子理所當然的作為。
但其實,內心的恐懼難以掩藏——
「我想長命百歲。」桃子說。
「我想活到連喜歡某個人的記憶也消失,等到即使我死了也沒有半個人察覺的時候,或許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如果出生就注定了死亡,那麼是不是只要留下被記憶的部分就足夠了?
直木賞大獎得主、備受期待的新生代作家 三浦紫苑
跨越時空、深入內心的驚艷之作
〈無愛〉——輝夜姬
〈火箭的回憶〉——開花爺爺
〈距離〉——仙女的羽衣
〈翠綠海灣〉——浦島太郎
〈抵達為止〉——頂鉢姬
〈花〉——猴女婿
〈令人懷念的河邊小鎮故事〉——桃太郎
作者簡介:
三浦紫苑,1976年生於東京。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系。
2000年, 以第一部長篇小說《女大生求職奮戰記》初次登上文壇。
2004年,《我所說的他》入選為「第18屆山本周五郎賞」候補。
2005年,《昔年往事》入選為「第133屆直木賞」候補。
2006年,以《多田便利屋》獲得「第135屆直木賞」。
《強風吹拂》獲選為「2007年日本本屋大賞」第三名。
另著有小說《月魚》、《祕密的花園》,散文《腐興趣》等作品。
譯者簡介:
張智淵
台北人,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課程修畢,從事翻譯十餘年,譯有《夢象成真》、《四疊半宿舍,青春迷走》(時報出版);《陌生的憑弔者》(圓神);《污點通訊》、《旋轉木馬》(麥田);《幽靈救命急先鋒》、《眾神的山嶺(上、下)》(繆思);《棄靈島》(春天出版);《所有男人都是消耗品》、《興趣無用論》(大田);《重力小丑》、《登山者》、《信》、《空中飛馬》(獨步文化);《布魯特斯的心臟》(皇冠)等三十餘本小說,以及多本心理勵志書,現為專職譯者。
E-mail:akiracat@seed.net.tw
章節試閱
沒有人記得我。
就連我都忘了自己。
心中只有一個聲音響起:
傳誦下去吧。
那大概就像是記憶。
接下來只會被人日漸淡忘。
無愛
輝夜姬
老爺爺在竹林裡發現了會發光的竹子。剖開一看,裡面裝著一名小女孩。女孩在三個月內長成亭亭玉立的姑娘,老爺爺替她取名為「輝夜姬」。五名貴族聽到美麗公主的傳聞,紛紛登門求婚。輝夜姬分別對五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沒有任何一個人達成;連聽到風評的皇帝也想召輝夜姬進宮,但是她予以拒絕,和皇帝僅止於書信往來的關係。
有一次,輝夜姬看著月亮哭了起來。她說:「我是屬於月亮的世界,下一次滿月的夜裡,會有人從月亮來帶走我。」皇帝派遣了許多士兵,但是在來自月亮的使者面前,完全束手無策。輝夜姬寫下離別信給老爺爺和皇帝,並且在臨走前留下長生不老藥,回到月亮上。皇帝心想,輝夜姬都走了,變成不死之身也沒有意義,於是在富士山頂燒掉了那些藥。
據說,我的祖父在二十七歲去世,我的父親也在二十七歲過世。而我,在上個月也二十七歲了。多謝妳替我慶生。
我的母親常說:「你父親一家人遭受了詛咒。」對於母親而言,我們家男人個個英年早逝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一家人都是窩囊廢」,所以遭到女人怨恨,縮短了壽命。
我不曾見過祖父,也不記得父親。我不曉得他們怎麼死的,反正是與我無關的往事。
不過,我只清楚地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因為舉辦法會,去參加父親這一邊的親戚聚會。那幕景象相當令我震驚;在場的盡是女人和小孩。不得不說,這些男人即使知道自己活不過三十歲,仍選擇在短暫的人生當中,迅速地讓女人懷孕留下子孫,果真是「不成材」的一家人。
祖父、父親連續兩代都死於二十七歲,由母親將我拉拔長大。她總是對我耳提面命:「二十七歲的那一年,你要少外出走動,謹言慎行」。那是我記憶中母親的最後一句話。不,我的母親並沒有去世,她在我讀小學時,和某個男人一起消聲匿跡,從此下落不明。外公外婆將我養育成人。對於他們而言,我的母親也是個十足「不成材的笨女兒」。
對於自己二十七歲的生日,我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舉例來說,假設NASA發表聲明指出:「明天,隕石要撞擊地球。」雖然害怕,但也無處可逃吧?內心或許會同時湧現難以置信和雀躍期待兩種情緒,想著「真的假的?!」以及「世界究竟會變成怎麼樣呢?會發生什麼事呢?」「二十七歲」對我來說,就是這種感覺。
即使到了二十七歲,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改變。像是切身感覺到內臟機能突然下降,或者千鈞一髮之際,閃過夜路上衝撞而來的暴衝汽車,諸如此類的事情什麼也沒發生。雖然感到失望,但是不管怎麼,我還是想活著跨越這個年齡;我一直沒有疏忽大意,實際上,我有工作和女友,所以也無法像母親說的那樣「謹言慎行」。
從妳沒有回我第一封簡訊,也沒有回電來看,妳大概正在呼呼大睡。現在是三更半夜,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吧。這樣也好,不要給我任何回應。因為打這些簡訊只是我的自我安慰罷了。只要想到一旦到了早上,妳會看到這封簡訊,我就稍微放心了。
話說回來,手指快抽筋了。這支手機到底一次能夠傳送多少字的簡訊呢?我並不喜歡小家子氣地打簡訊,即使連絡客戶大多打電話長話短說,也幾乎不曾用過簡訊功能。就算用也頂多只是傳「昨晚很愉快」或「最近在做什麼」。
如今,我讓不常使用的大腦全速運作、用手指拚命按鍵,祈禱妳不會不跟我說一聲,就換掉電子郵件地址,導致這封簡訊變成無主孤兒。
沒時間了,我就進入正題吧。
我現在躲在晴海碼頭的倉庫裡,坦白說,我有生命危險。城之崎組的一幫傢伙拿著手電筒,正在四周鬧哄哄地找我。這種場景太老套,連我自己都笑了,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倉庫內悶熱得要命,讓我喉嚨乾渴。
妳或許會覺得詫異,別打簡訊,打電話報警不就得了。但是,那幫流氓說:「你有膽向警察求救看看!我們就殺了你住在鄉下的外祖父母!」
那種老頭子、老太婆,要殺請便!反正即使你們不動手殺他們,他們也已經一腳踏進棺材了。我想這麼告訴他們,但終究還是無法報警。那幫傢伙說到做到。我不想讓養育我的外公外婆慘遭殺身之禍。
看來我和祖父、父親一樣,逃不過「二十七歲的詛咒」。二十七歲之後,我自認為十分謹慎地生活,但到底是誰對我施加了這樣威力強大的詛咒呢?
事情始於上個月的生日。
因為是一年當中最賺錢的時刻,所以我滿場穿梭、到處坐檯,伺候芳心難耐的女人。這種大日子的夜裡,我可沒有笨到承諾特定的女人在打烊後陪她。我像隻花蝴蝶般翩翩飛舞,一心一意要在早上之前儘量多吸點花蜜。
樓層內充滿了香氣逼人的艷麗花朵,女人們激烈競爭,對我展開送禮攻勢。有人開酒;有人遞出包裹。我若無其事地以目光估算那些金額,對所有女人道謝。
我保持冷淡,好讓她們曉得「這麼點禮物滿足不了老子」;隨著金額大小,微微調整嘴角浮現的笑容弧度。
有些人一旦知道我的工作,就會一臉神氣地給我忠告:「別把別人的感情換算成金錢,或者秤斤論兩地變賣愛情。」不知為何,會說那種話的以男人居多。每次去高中同學會之類的活動,就會被煩得半死。
我並沒有變賣愛情,只是販售等價的服務。而且,金錢也能夠表達心意吧?否則的話,為什麼世上和金錢牽扯不清的糾紛如此之多呢?因為金錢是心意的表徵,所以金錢投射出了人的背叛和憎恨,不是嗎?
對於這些大可以投稿到報紙讀者欄的寶貴意見,我會洗耳恭聽,然後告訴對方:
「你老婆從剛才在就那裡抱怨,說『我老公錢賺好少,真是傷腦筋。他倒也不是沒責任感,但是我從他身上感覺不到愛。我覺得當初結婚實在太衝動了。』」
或者,也有人會嘻皮笑臉地說:「受女人歡迎真好。」這種揶揄和羨慕是個誤會。
天底下沒有「受女人歡迎的男人」。相反地,也沒有「受男人歡迎的女人」。我純粹只是「受到喜歡像我這種男人的女人歡迎」而已。受歡迎的範圍有限。認為自己受異性歡迎的人,只是沒有察覺到自己的魅力只適用於非常狹窄的範圍。若是弄錯這一點而沾沾自喜,根本不適合這種工作。因為必須熟知自己魅力的射程範圍,有效地狙擊客人。
我悉心照料的客人有五位。生日晚上,五人當然都來店裡光顧。
六十多歲的家庭主婦─石田。聽說老公是中小企業的社長,她有錢又有閒,是典型的「帶大小孩就人老不中用、沒見過世面的賢妻良母」。她對待我的態度時而是思春期的國中生,時而是愛瞎操心的母親,兩者輪流交替,但是我並不討厭她。
那一晚我一坐檯,石田便一如往常地臉頰飛紅,問我:「你有沒有乖乖吃飯?」我將手臂靠在沙發椅背上,順勢悄悄地將手掌搭放在她肩上。我悶不吭聲。石田因為太過緊張而聲音顫抖地說:「我有禮物要送你唷。」
石田從黑色波士頓包中拿出來的是一尊佛像。約莫紅酒瓶的高度,表面的金色熏黑了。
我和包圍茶几的助手們都傻眼了。石田說明,那是很難買到手、有價值的佛像,但是年輕的助手都明顯在憋笑。
或許我原本該怒斥石田:別讓我丟臉!不過,連我自己也拚命壓抑想大笑的衝動。我是第一次收到這種禮物。我不懂佛像的價值,但嘴角八成皺起了大笑的皺紋。我道了聲謝,立刻離開了那張桌子。
倉持一身和服裝扮,在樓層中央的桌子等候我的臨幸。
「我買了你想要的賓士鷗翼跑車。金屬銀的唷。」她說。
我瞥了放在茶几上的車鑰匙一眼,說了句「謝謝」。助手說:「哇啊,真棒耶。」對我露出打從心底感到羨慕的眼神。
「我不會載你唷。」我笑道。
「哎呀,那我呢?」
倉持放鬆粉底開始浮起的四十多歲肌膚,看了我一眼。
「改天我送媽媽桑到妳的店吧。我再打電話給妳。」
我小心不弄亂她梳整得一絲不苟的包頭,在她的耳畔呢喃。
阿部是上班族的妻子。我不曉得她找了怎樣的藉口,在晚上溜出家門。
小錢累積起來也是一筆為數可觀的金額。助手之間流傳,她可能籌措了家中生活費,砸下打工的收入,搞不好還借錢上門光顧這家店。不過,那是她的問題,與我無關。因為我不曾向她索取什麼。
助手對我講悄悄話,說阿部點了十萬圓的香檳王,我從倉持的座位起身轉檯。阿部的座位四周也有不少隨侍在側的助手,或許是心理作崇,我總覺得連燈光也很昏暗。
「晚安。」
我讓身體深深地陷入沙發,像是要從底下仔細看阿部的臉。這種女人會鎮懾於金碧輝煌的場地,整個人縮成一團,所以必須儘量提振她的自尊心,讓她放鬆緊繃的身體。這麼一來,她就會像工蟻般辛勤地搬運糧食過來。一次的量不多也無所謂。
「生日快樂。」阿部說。「希望這個適合你。」
她遞出一個盒子。裡頭八成裝著襯衫。一眼就看得出來是阿曼尼。我對陪坐在座位角落的新進助手說:
「你不是在嘀咕襯衫不夠嗎?這個送你。」
新進助手慌張地輪流看著我、襯衫的盒子跟阿部,嘟嚷道:「可是……」阿部臉色蒼白地看著情勢演變。
「我和你的身材差不了多少,你應該穿得下吧。」
我再三堅持,資深的助手彷彿明白了我的用意,以阿部也聽得見的音量代我對菜鳥說:
「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人和你不一樣,只穿訂製服。他的更衣間可驚人了。一整排襯衫。你就不要客氣,儘管收下吧。」
「謝謝。」
菜鳥抱著襯衫的盒子,對我和阿部低頭鞠躬。特地買的禮物被我轉手送人,阿部差點哭出來。我摟住她的肩,將香檳王倒進酒杯,送至她的唇邊,順勢悄悄對她說:
「託妳的福,我在小弟面前也有了面子。謝啦。」
我從沙發起身,頭也不回地前往下一張桌子。助手們大概會教育她,假如希望我穿上妳送的衣服,就得更努力才行。
女大學生伴會用父親的錢上門光顧,據說她父親是公司的董事。不曉得是一家多麼賺錢的公司,但我認為,對女兒採取放任主義也該適可而止,否則猛然驚覺時,就得擔心老後的生活了。伴對錢揮霍無度的程度,令旁人看了都不禁替她父親擔心。我遲早想獨立門戶開店,所以想趁油水飽滿時,從伴身上多榨一些出來。
但是那一晚,伴說:「我被爸爸發現了。
「我想,我不能再來了。」
伴從手提包中拿出三百萬,放在茶几上,說:「你拿這些錢去買手錶。不要忘記我唷。」
「感恩。妳別突然送我這麼大的生日禮物嘛。」
我說,叼起香菸。助手立刻從旁替我點火。伴是個笨蛋,所以聽不懂諷刺的話。
「很大吧?我拚命設法湊到的。」
天真無邪的態度像是等待獎賞的狗。
助手在最內側不醒目的桌子,高聲說:「九四年的羅曼尼﹒康帝。感謝消費!」一瓶一百二十萬。
我隔了半晌之後站起來,走向內側的桌子。伴嬌聲地發牢騷:「你這麼快就要走了嗎?最後一次見面了說。」我當然甩都不甩她。在伴的座位坐檯的助手趕緊安撫她:「他馬上就會回來了。妳看,他把香菸放在這裡沒拿走。不管怎麼說,他最喜歡的就是伴小姐了。」智障,那包香菸盒空了。別理她就好了,用不著連不會再來的女人,都按照待客手冊以禮相待。
我心浮氣躁地從樓層負責人手中接過新的香菸,到內側的座位坐檯。
神保是個美女。她說她三十二歲,但有時候看起來比我更年輕。不過,她偶爾看起來又比聚集在這家店的任何一位客人老成。
神保看到我走過來,以熟練的動作將羅曼尼﹒康帝斟入酒杯,從茶几上滑到我面前。
「謝謝。」
我稍微淺抿一口,說:「好酒。」
神保是做什麼的女人呢?我小心翼翼地打探,但實在摸不著頭緒。可以肯定的是,她不是良家婦女,好像也沒有光顧其他家店。
做這一行最該避免的是被捲入男女感情的糾紛裡。但是,神保既不曾帶著護花使者來店裡,也沒有被某個男人包養的那種女人特有的惴惴不安,或是反過來享受刺激的緊張感。
大部分的女人起碼都會死皮賴臉地央求一次,但她非常聰明,從來不會叫我去她家,或者說她想來我家;總是不動聲色地來店裡,花錢、跟我聊天,然後渾然忘我地上賓館。
神保沒有喝助手倒的酒。
「妳不喝嗎?」我問。
問的那一瞬間,我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神保應該是菸一根接著一根抽,抽菸的速度連訓練有素的員工都來不及換菸灰缸才對。但是這一晚,我還沒看到她優雅地抽菸。
「我想了很久。」她以砂紙磨亮般的嗓音說。
只有抽菸抽壞的喉嚨才發得出那種聲音。
「我決定送你孩子當作禮物。」
「那是什麼意思?」
我隱藏內心的慌張,努力冷淡地說。我知道助手們倒抽了一口氣,滿懷好奇心地豎起耳朵。
「你不是說,你想趁早有孩子嗎?我有了。」
神保依舊面無表情,以左手撫摸自己的腹部。我坐在她的右手邊,溫柔地把手放在她腿上,小聲地制止她:
「別開玩笑了。」
當時,我嚴詞拒絕神保:「管妳是不是有了小孩,都不關我的事!」她在黎明時分終於離開了店。一如往常地,被女人折騰得半死的夜落幕,我去妳的公寓。妳記得自己當時已經起床準備上班,說要慶祝生日,煮了早餐給我吃嗎?那是我那一天收到的禮物當中,最便宜的一項。
我想,妳現在應該對我在深夜寄的一堆莫名奇妙的簡訊,感到狐疑和擔心。不過,沒有任何事情會對妳不利,所以我希望妳放心地繼續往下看。
我至今也完全不認為自己犯下了決定性的失誤。
印象中,我確實對神保說了:「雖然從事這種工作,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我遲早想要個孩子。」這充其量只是作為「和家人緣薄男人的故事」,所說出的選擇性發言罷了,當然也是服務的一部分。我並沒有說「希望妳替我生孩子」,更重要的是,我隨時做好了萬全的避孕措施。
即使神保真的懷孕,也不可能是我的小孩。雖然凡事不能斷定百分之百,不過我可是職業的,對於那種事情相當小心。我想說「妳儘管去驗DNA」,但是這招對她不管用。
手掌因為汗水而變得黏滑了起來。我累了,我要休息一下。
我說過了,我躲在倉庫裡吧?地板是水泥,天花板非常高。晚上漆黑空曠的倉庫的光源,是手機白裡透青的液晶螢幕,和從靠近天花板牆壁上的一排小窗戶照進來的街燈。等眼睛習慣黑暗之後,我發現堆積的瓦楞紙箱中裝的是個人電腦。大概是在中國或某個國家組裝的便宜製品。
耳邊傳來遠方奔馳的車聲,以及每次船經過就會拍打碼頭的海浪聲。明明兩者的聲音飄渺,但有趣的是,聽得一清二楚。除此之外,還有夾雜其中、好幾個人在找我的腳步聲。
說到這個,我記得妳曾說過,每天早上都會看電視上的占卜單元。妳相信命運嗎?
……經過仔細思考,總覺得這和問妳相不相信愛情一樣,是個令人害臊的問題。
我不願相信命運或愛情。因為我兩者都沒看過。或者應該說,當我想到「那或許是愛情」時,就已經錯過了。那種東西,有跟沒有一樣。就像隕石撞擊地球一般。
撞擊後,一切也結束了。
二十七歲之後的一個月,我持續過著和之前沒兩樣的生活,但是那段期間內,情勢每況愈下,就像是抓在手中繩索的細纖維,一根根地靜靜斷裂。或許我經常遭到命運之神遺棄。
伴如她所說,自從生日那一晚之後,她再也不來店裡。我打過一次電話給她,問她「妳好嗎?在做什麼?」暗示她來店裡。但是伴說:「我覺得學到很棒的社會經驗。雖然被爸爸痛罵了一頓,但是過程很愉快。」我錯失了一名客人,但是我沒有死纏爛打;做這一行要是被人看輕,可就沒戲唱了,貫徹去者勿追的精神很重要。
驚人的是,阿部的先生翹辮子了。阿部像平常一樣上門,在我坐檯的同時,她說:
「我老公自焚身亡了。」
一副沒什麼大不了的樣子。我馬上想起了那一週前,刊登在報紙上的報導。內容提到一名任職於區公所的男子,以負責產業廢棄物相關的部門工作為苦,在多摩川的河岸地潑灑柴油引火自焚。報紙「盛大地」處理這則新聞,說真的,這種做法實在很不得體,更別說還有追究這起事件背景的專題報導。阿部的老公大概每天過著踏實的日子。他的那種死法,不適合樸素的阿部。
「辛苦妳了。」我說。
阿部把臉頰靠在我肩上,陶醉地說:
「我老公有留下一點遺產,而且聽說可以領保險金。我問你,要不要一起去旅行?」
開什麼玩笑?!
「真遺憾,我沒有時間。妳大概身心俱疲,不妨一個人去放鬆一下。」
我不想被捲進麻煩事之中,卯足了勁推辭。阿部一反常態地表現積極。或許是可望拿到不少錢,她甚至提議要我下班之後陪她。這是她平常不曾說出口的。
「今天不行。我有點感冒,我想直接回家睡覺。」
這麼說她也不相信。不得已之下,我只好提議:
「不然,妳送我回家吧。」
阿部一起坐上了計程車,到我距離店裡二十分鐘車程的公寓。她跟著上樓到我的住處門前,我向她道晚安,然後關上大門。聽見我掛上門鏈的聲音,她才終於接受了。我從客廳的窗戶,確認阿部坐的計程車開走。
沒半個好客人。
我馬上走出家門,到馬路上攔了一輛計程車回到店裡。因為倉持有預約。
「你去哪裡了呢?」
倉持一臉倦容地大發牢騷,像是晚支付薪水,以致店裡的女孩們不聽指揮。
還不是為了買車給你。你好歹多陪我一下嘛。一連串的怨言沒完沒了,於是我大喝一聲:「妳少自以為了不起!我可沒拜託妳買車給我。」結果,倉持終於安靜了。
鞭子之後,需要胡蘿蔔。那一晚,我陪了她好久,身心俱疲、心情鬱悶。後來我立刻把鷗翼跑車變賣,換成了現金。
只是,麻煩事依舊持續。
我辦理賣掉鷗翼跑車的手續,順便想把石田送我的佛像換成現金。佛像這種玩意兒,和我家的裝潢風格實在不搭調。
車子被開走後,我花了一天的公休時間,尋找適合的古董藝品商。因為沒有特別的門路,只能在銀座後巷裡,向一位正拉下店裡鐵捲門的老爺爺詢問。
極度沉默又對人愛理不理的老爺爺請我進入店內,仔細地端詳佛像,開了一個買進價格。意想不到地高。
「成交。」我故意態度冷淡地說。
那一瞬間,老爺爺的眼睛為之一亮,令我再度明白老舊的佛像價值不菲。無所謂,反正是別人送的,成本是零。臨時的一筆收入令我相當開心。我按照老爺爺說的,在買進帳簿上填寫自己的姓名住址,另外還需要查看身分證,我也乖乖地給他看駕照。
三天後,警察登門造訪。我在睡覺時被叫醒,警察問我是在哪裡買到那尊佛像的,看來似乎是贓物。古董藝品商的老爺爺意識到,那很像某間寺廟在幾年前遭竊的佛像,發揮僅有的一丁點良心報警。真是的,保持沉默賣給別人不就得了。
我解釋是客人送我的生日禮物,告訴警察石田的聯絡方式。竟然送我麻煩的東西,我對爛好人一個、不諳世事的石田感到滿腹怒火。
警察好像向石田詢問了來龍去脈。當然,我想她並不知道那是贓物。不知是氣我轉賣佛像,或者花錢在我身上被老公發現,總之她沒有再來店裡。
助手們說:「你最近好像很衰。」沒有人會真心同情或擔心我。因為有人吃鱉,自己的業績就會相對成長。
人聲靠近了。城之崎組的搜索人員似乎來到了隔壁的倉庫。我心想,幹嘛不乾脆快點找到我。那麼一來,我也不用一直恐懼緊張。
小時候,玩捉迷藏時,我喜歡一面躲在圍牆後面,一面偷偷地站著小便。這是因為等待鬼的過程中,心情會非常亢奮,但又不知如何打發時間,就會憋不住尿意。妳不會這麼做嗎?小女生不會在外頭小便嗎?
心裡害怕加上這裡十分悶熱,從剛才就流了好多汗,現在完全感覺不到尿意。
運勢不順時,我會改變放錢的地方。今天拿著原本放在家中角落的紙袋,準備前往車站前面的銀行。紙袋中裝著上個月的薪水和賣掉佛像的一疊現金,以及賣掉鷗翼跑車後,剛入帳的銀行存摺。
公寓外面停著一輛大型的白色賓士。我沒看過這輛車。原本打算把錢存到銀行,或許是一種預感,讓我改變了心意。假裝紙袋中裝著換洗衣物,動作自然地將紙袋寄放在車站的投幣式置物櫃。接著我到便利商店買信封和郵票,在羅多倫一面喝咖啡,一面在信封寫上收件人姓名,將寄物櫃的鑰匙放進信封,仔細封口後,投入郵筒。
順路搭電車,準時在預定的時間去上班。
當我知道神保是城之崎組幹部的情婦時,已經太遲了。城之崎組的一幫傢伙找上門,將我強行帶走。對方是三個人,命令我跟他們到堂口去一趟。我險些被押上車,雖然逃走了,卻又在我混入新宿車站人群的前一秒鐘被逮住,把我抓進居酒屋內側揍得鼻青臉腫。
「等一下!」我說。「你們誤會了。」
話還沒說完,我的臉又挨了一拳。鼻梁骨折,黏膩的鮮血一口氣流到下顎。也從內側灌進了喉嚨。
戴著大金戒的男人露出同情的眼神,看著癱坐在路邊的我。
「事到如今,是不是誤會都不重要。問題在於田山老大火冒三丈,說你讓他顏面掃地。你懂不懂?田山老大非常生氣。說要把你丟入東京灣。」
「我不知道。我一點都不知道她是你們田山老大的女人。」
男人彎下腰來,用指尖捏住我的鼻子,小心謹慎地把骨折的骨頭移回原本的位置。這痛得要命,而疼痛化為一聲悶響,響徹了整個頭蓋骨內。
「快點,走吧。」男人說。
我被押上車載走。
「可以用錢了事嗎?」我問。
「兩億。」男人回答。
我拿不出那麼多錢。換句話說,他不打算救我一命。車沒有前往堂口,而是往海邊開去。在下車的那一瞬間我趁機逃走,鑽進了一間倉庫,直到現在。
沒有人記得我。
就連我都忘了自己。
心中只有一個聲音響起:
傳誦下去吧。
那大概就像是記憶。
接下來只會被人日漸淡忘。
無愛
輝夜姬
老爺爺在竹林裡發現了會發光的竹子。剖開一看,裡面裝著一名小女孩。女孩在三個月內長成亭亭玉立的姑娘,老爺爺替她取名為「輝夜姬」。五名貴族聽到美麗公主的傳聞,紛紛登門求婚。輝夜姬分別對五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沒有任何一個人達成;連聽到風評的皇帝也想召輝夜姬進宮,但是她予以拒絕,和皇帝僅止於書信往來的關係。
有一次,輝夜姬看著月亮哭了起來。她說:「我是屬於月亮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