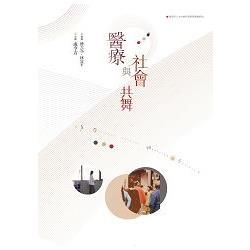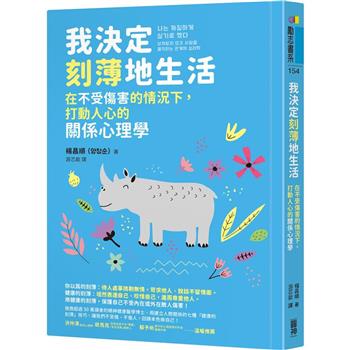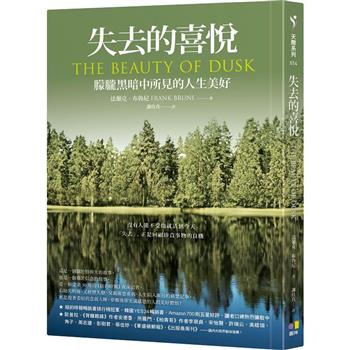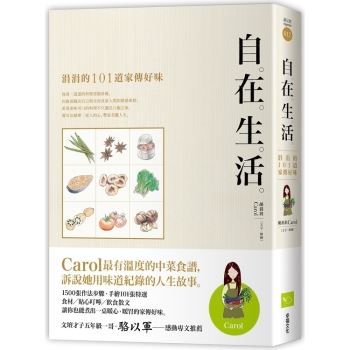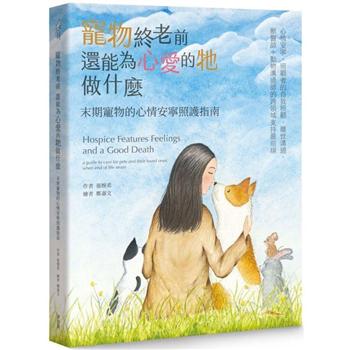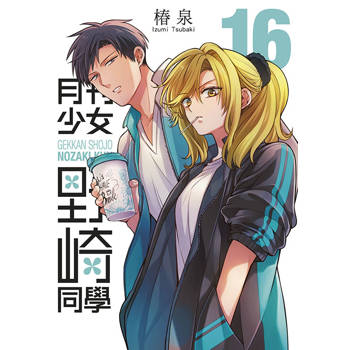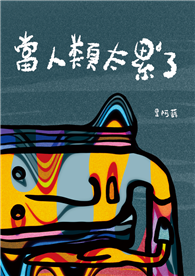當醫學遇上社會學,究竟會碰撞出什麼樣的火花呢?本書邀請了國內三十三位生物醫學界和社會人文學界學有專精的學者與教授,以日常生活中的醫療、健康實例做為主題,將他們多年的學術研究轉譯成趣味盎然,淺顯易懂的短文,使讀者能在醫療中看見社會的多重意義,破解以為「醫療中立,不受社會影響」的迷思;使讀者能進一步瞭解,醫療為達到維護眾人健康的目的,必須正視醫療領域中知識、權力關係的不平等,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等議題。
本書共分成「另類醫療」、「醫療專業的興起與變遷」、 「醫學知識與權力」、「醫療政策與市場」、 「身體經驗」、「工作與健康不平等」、 「醫療技術」、「風險與醫療爭議」等八大篇, 篇篇精彩的文章帶領讀者,從醫療社會學、公共衛生、以及科技與社會的視野,思考、審視「醫療與社會」的關係,期盼本書能激發更多的對話與創見。
作者群簡介
成令方
學歷:英國 Essex 大學社會學博士
經歷: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研究興趣:性別社會學、醫療社會學、工作社會學、質性研究、性別與科技
傅大為
學歷:美國Columbia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博士
經歷: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清華大學歷史所教授(科技史組與STS組)
研究興趣: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台灣當代文化史、性別與醫療╱科學、性╱別、台灣近代醫學史
林宜平
學歷: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
經歷:台大公衛學院健康風險及政策評估中心助理教授、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專案計畫助理教授
研究興趣:環境╱工作╱健康、風險管理與溝通、醫療人類學、社會流行病學、科學╱科技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