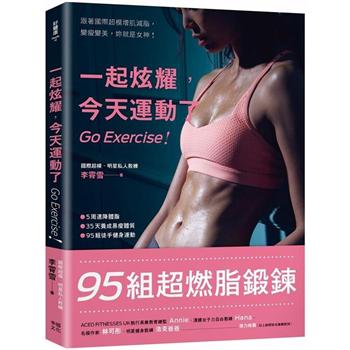推薦序
愛、熱情與冒險∕劇場編導 魏瑛娟
十九世紀法國寫實主義作家及詩人亨利.穆傑(Henri Murger)以自己年少與朋友的青春軼事寫成了著名小說《波希米亞人》(Scenes de la Vie de Boheme)。這系列如社會紀實的生活篇章,展現了十九世紀浪漫青年不受羈絆的生活價值觀及對藝術與愛的熱切追求。 反抗傳統、熱情於生活、在平庸裡創新冒險、愛與藝術至上、自我的流放、重塑與認同……這些由小說角色們靈活展現的性格特質與生活企求,深深打動讀者,也在作者的推波助瀾下,「波希米亞人」成了一專有名詞,更代表了某種精神態度,提供了浪漫綺想,吸引無數想自平凡庸常生活裡逃脫的叛逆之士。
波希米亞人雖原指捷克境內波希米亞地區族裔,但因種族複雜,政治變遷,且與吉普賽人勾連,後成了化外族群同義詞。亨利.穆傑延伸其義,大加渲染發揮大眾對其浪遊狂放的誤解與想像,在書中以詩人、音樂家、畫家與哲學家等四位社會邊緣(也浪漫)角色重書定義。《波希米亞人》呈現的如一天真率直美好生活繪畫捲軸,迆邐開來的是不畏現實艱險與挑戰的青春喜劇,充滿愛、熱情與冒險,即使角色並不全然圓滿收場。波希米亞精神或波希米亞人成了無可抵禦魔幻呼招,挑動許多不安於現狀的創作者回應與附和。歌劇大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鍾情其愛情篇章,節選強調愛情的美麗與悲傷,譜出膾炙人口的歌劇《波希米亞人》,高唱愛是生活裡最熱情的冒險。近年更有百老匯音樂劇與電影《吉屋出租》(Rent)的製作與生產。對愛與藝術的追求主題當代化,探討了同性戀、愛滋與跨性別諸多議題,在禁忌與邊緣裡質疑威權和主流,現代化了波希米亞精神且更新了波希米亞人形象。
「每個屬於波希米亞人的人,從文學家至職業密謀家……他們或多或少地處在一種反抗社會的低賤地位上,並或多或少過著一種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在他的夢中不是孤獨的,他有許多同志為伴。」班雅明如此論述波希米亞人,贊同波希米亞精神,猶如人類單調平庸生活裡的救贖與出路。低賤甚或有傾滅疑慮,但那是無法抑止或抹去的美好抗逆精神,冒險帶來生機,靈魂得以繽紛,得以自由。
作者序(節錄)
本書所描繪的波希米亞人,並非是通俗小說家筆下的強盜和刺客,也非來自跳舞熊藝人、吞劍者、打零工的守衛、賣彩券的街頭小販和其他成千上萬界線模糊的神秘職業。他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沒有工作,但在此同時,只要有好處,他們又什麼都可以做。
這些波希米亞人並非現代才出現的族群,他們存在於所有時代、所有地區,綿長的血統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沿著波希米亞的族譜上溯,在古希臘時期,一位赫赫有名的波希米亞祖先曾在富裕的愛奧尼亞境內漂泊,享用慈善的麵包,並在好客人家的爐火旁彈奏他的七弦琴,吟唱關於海倫的愛情和特洛伊陷落的歌曲。時至近代,當代波希米亞人可以在所有的藝術和文學領域找到前代的蹤跡。在中世紀,吟遊詩人、民謠作曲家、尋歡思想的子嗣、歌聲動聽的都蘭流浪者等,這些流浪樂手們延續荷馬的傳統,攜著乞丐般空空如也的錢包、背著樂聲悠美的豎琴,一邊歌唱,一邊穿越克萊門斯伊索爾那盛開著雪白玫瑰的美麗原野。
在騎士精神和文藝復興之間的過渡期,波希米亞人繼續在國境與國境間遊走,少部分的人在此時來到了巴黎。例如皮埃爾.格蘭戈爾,流浪者之友與禁食的敵人,他面黃肌瘦,彷彿一生都處於永恆無盡的齋戒期。他在城中落腳,靈敏的鼻子四處追尋著廚房和餐廳飄出的食物香味。他光憑著飢腸轆轆的眼神,就足以讓肉舖外吊著的火腿變小,想像力在他的腦中叮噹作響--可惜,同樣的聲音沒有出現在他的口袋中--那是他辛辛苦苦地為路易九世寫完一齣戲後,參事答應支付給他的十克朗報酬。相較於愛斯梅達那陰鬱愁苦的愛人,波希米亞編年史裡出現了另一個少了些禁慾色彩、面容歡快的角色--法蘭西斯.維庸,一個貨真價實的天才和流浪者,他的詩句中滿溢著豐富的想像力。維庸被奇妙的欲望所支配;古代詩人或許會稱之為命運--他的行為帶著他一步步接近絞刑架,據說他曾因為太靠近「欣賞」王冠的顏色而被逮捕,不過他後來逃脫了--這個維庸可不只一次逃過守衛的看守。他是皮爾街上最吵鬧的住客、埃及公爵晚宴上最雀躍的人、韻文界的羅薩;他的詩句包含著令人心碎的感傷和最真誠的語調,在一旁的謬斯被感動的淚水淹死之前,就足以打動最無情的惡棍和流浪漢,讓他們徹底忘記貪婪、殘忍和浪蕩。
在那些對認識有限、只知道「『馬勒布來了』揭開了法國文學序幕」的人之外,一群默默無名的人已經開始踏上了維庸勤耕的土壤--其中不乏詩壇上聲名顯赫者,他們掠奪他為數不多的遺留財富,並以之創作出屬於自己的榮耀。那是波希米亞吟唱者在冷天屋簷下、用顫抖的雙手寫下的民謠,破舊茅屋裡傳出、散發著謬斯靈光的即興詩句,這些作品在今天,紛紛染上了琥珀的色澤和麝香的氣味,變質為貴族徽章邊上的精巧紋飾。
文藝復興盛大揭開序幕。米開朗基羅正登上西斯汀教堂的鷹架,神情緊張地看著年輕的拉斐爾手拿壁畫的草圖,步上梵諦岡的臺階。切里尼在柏修斯像前沉思、吉爾貝蒂雕刻著洗禮堂大門的紋飾、多納太羅在亞諾河大橋打磨著大理石。接著,梅第奇的市民崛起,儼然與李奧十世、尤里烏斯二世相抗衡;許多重要作品出現在他們手中--提香和韋羅內塞為總督府畫上奪目的色彩,在他們的畫筆下,聖馬可大教堂足以和聖彼得大教堂相匹敵。
這場天才狂熱從義大利半島爆發,迅速延燒至整個歐洲。藝術挺身反抗上帝,與帝王們並肩齊行。查理五世彎身撿起提香的畫筆;法蘭西斯一世出現在印刷廠的舞會上--多雷此時可能正在那兒校對原稿。
而在這眾聲齊放的時代,波希米亞人的蹤影依然可見;就像巴爾扎克小說裡形容的:他們遊走在生活邊緣,尋找下一頓晚餐和可以遮風避雨的屋簷。克萊門.馬羅穿梭在羅浮宮中,深受美麗的黛安娜寵愛--這位法國國王的情婦,微笑照耀了三個朝代。之後,不忠的謬斯將他從黛安娜的起居室引至了王姊瑪格麗特的接待間,而這充滿危險的善意,終於為他招致了牢獄之災。同一時期,另一位波希米亞人塔索--他的童年在拿不勒斯的索羅托海濱度過、並受到詩神的眷愛--也走進了費拉拉公爵的城堡,只不過他沒有黛安娜和瑪格麗特的寵兒幸運,這位偉大長詩《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作者,最後因為對埃斯特家的女兒大膽示愛,付出他的理性和所有天才作為代價。
梅第奇家族進入法國,引發了一連串的宗教和政治風暴;但這些都沒有影響到藝術的蓬勃發展。這段時間,雕刻家古戎在〈無邪之泉〉的鷹架上找到了異教徒菲狄亞斯手中的鑿子;詩人龍薩則重拾希臘吟遊詩人平德爾遺落的七弦琴,和詩社友人一同創立了法文的詩歌學院。這所學院與馬勒布及其門徒的信仰相呼應,試圖將法文書寫中那些因為希臘化而產生的的異國風格清除乾淨。波希米亞人雷尼耶,詩歌堡壘最後的捍衛者,以修辭與文法作為後盾,公開指稱拉伯雷的粗俗野蠻和蒙田的晦澀難懂,這位諷刺者同時為羅馬古詩人荷瑞斯的嘲諷增添新意,在他的時代憤怒疾呼:「榮耀不過是過時的老聖人祈禱的東西。」
十七世紀的波希米亞人名單,包括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治下不少文學界的名字。他們是出沒在朗布依埃夫人沙龍的常客、曾參與傳奇詩集《茱莉的花束》的製作,他們有管道自由進出巴黎皇家宮殿,並和專政中保持自由立場的宮廷詞臣共同創作。他們在瑪莉翁的躺椅寫滿情詩,在皇家廣場的樹下向妮儂求愛;他們清晨在『暴食者』或『皇家寶劍』等小酒館用餐,晚上則在宮廷顯貴的晚宴桌旁停留,在街燈下為了約伯或烏拉尼亞的十四行詩拔劍決鬥……波希米亞經歷了愛情、戰爭甚至外交,此時開始對冒險心生倦意。他們著手把新約和舊約轉寫為詩,成為領有薪俸的一群人:他們成為肥胖的牧師、甚至戴上了主教的王冠,有些人則在不久後成立的學院裡謀得安定的位置。
十六到十八世紀間,出現了兩個偉大的天才。他們身處於海洋兩端的遙遠國度,但在文學上面臨的對抗和掙扎卻無比相似--他們是莫里哀和莎士比亞,這兩個最傑出的波希米亞人,擁有極其相似的命運。
到了十八世紀,文學界最重要的名字同樣能在波希米亞的系譜上找到;其中光芒最為耀眼的兩人是盧梭和達朗貝爾--後者在出生時被遺棄在聖母院的石階上。而在面容模糊的波希米亞群體裡,麥爾費拉特和吉爾伯特兩人受到了過度的讚揚:前者的靈感不過是盧梭抒情詩的微弱反照,後者的思考則是無謂的傲慢和仇恨的組合,在裡頭甚至找不到一絲原創或真誠;因為他的聲音,僅只是作為派系鬥爭的工具。
分散各時代的波希米亞家族簡介,將在此告一段落。我們之所以刻意將這一長串的名單放在序言最前面,是為了避免讀者在初次接觸「波希米亞人」這個名詞時,所可能產生的一些誤會。隨著書中對波希米亞人在習慣和語言上的深入探討,讀者將能明白一般人普遍對「波希米亞」一詞,有著相當程度的誤解。
在今天,一如往昔,任何一個有志以藝術為天職、且除了藝術天分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的人,都注定將踏上波希米亞王國的小徑。贏得各種獎章的知名藝術家們,大部分都曾是波希米亞的一員,而他們在晚年的富裕與榮耀中,仍然時常回想起(或許帶著些微的遺憾)當他們攀爬青春的翠綠小坡時,他們只有二十多歲,除了勇氣之外一無所有--勇氣是年輕的特權;而希望,就是窮人的財富。
對那些開始感到不自在的讀者、膽怯的市民和諸多無法確切定義的廣大群眾,我們將重述我們的真理:
波希米亞是藝術的必經之路;它是學院的前奏、休養的殿堂、以及靈魂的最終歸屬。
我們還要補充一點:波希米亞的生活方式,只有可能存在於巴黎。
接下來,我們將談及絕大多數不為人知的波希米亞人。這個由窮困藝術家組成的龐大家族,彷彿受到了失去姓名的詛咒,既不能也不知該如何引來一絲的名氣,好證明自己藝術中的地位;或是透過他們已有的,展現自己可能的未來。他們是最頑固的夢想家,最熱情的信仰者,對他們來說,藝術是信念而非職業:只要看見真正的傑作,就能讓他們興奮不已;他們真摯的內心,為了不需名稱與流派的存在之美而加速跳動。波希米亞人是那些擁有偉大夢想,並將之付諸實踐的人,而非粗心、膽小、安逸的人,或是不切實際、幻想著工作會自動完成的人,更不是那些投機取巧、想靠著手段贏得名聲和財富的傢伙。
……
藝術的戰場一如所有戰爭,勝利的光環屬於領導者,而軍隊裡的小兵只會受到一點口頭上的鼓勵。在戰場中倒下的士兵,被埋在他們的葬身之地,一個墓誌銘上記載了兩萬個死亡的名字。
群眾也是如此,他們的視線永遠集中在初升的太陽上,從來不曾稍微低頭看見那些為數眾多、面孔模糊、正在地下世界努力奮戰的人們。許多人至死沒沒無聞,努力一生的成果甚至得不到一個鼓勵的微笑,只有冷漠陪著他們離開世間。
……
真正擁有力量的心靈總有話要說,而或早或晚,他們終將找到自己的聲音。天賦或才能並非是人性的單純偶然;他們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不會永遠沒沒無聞。就算人群不曾來尋找他們,他們也一定會被發現--天才就是太陽,所有人都看得到。才能則是鑽石,或許會隱藏在地底深處很長一段時間,但總會有人發現它。因此,我們不需浪費時間去為那些無味的短詩、虛假的哀歌感到惋惜,因為寫出這些東西的人,不過是懶惰、放蕩、無用,誤闖這個世界並糟蹋藝術家名聲的波希米亞寄生蟲。
一句格言說:「不為人知的波希米亞並非通道,而是條沒有出口的死巷。」
的確,這種生活不會帶來任何結果。這是種單調而愚蠢的悲慘,身處其中,智慧有如失去空氣的油燈,悄然熄滅;跳動的心因為強烈的厭世而逐漸變得毫無知覺;人類最美好的本質轉變成了最糟糕的。如果一個人不幸被困在這樣的死巷中太長太久,就會再也無法脫身,就算冒著危險勉力脫逃,也只會落入另一個臨近的波希米亞王國--文學和藝術在那裡並不當家。
……
現在,我們將一同走進真正的波希米亞王國,這是組成本書的主要元素,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本書的主題。真正的波希米亞人的確受到了藝術的召喚,並且有機會可以成為那些被選上的藝術家。波希米亞人和其他人一樣,生活在重重危險之中;在他的左右兩側有兩道深淵:貧窮和懷疑。在這兩道深淵的中間,一條細長的路通往波希米亞人的目的地。他們可以用眼睛看見他的目標,只是還在考慮恰當的抵達時間。
部分波希米亞人已經正式公開了波希米亞的存在,不過,國民的名字並非照慣例記在戶口名簿上,而是,引用自其中一位波希米亞人的話:「名字都寫在(還沒付清的)帳單上。」這群人正開始文藝界上打響波希米亞人的名號。
為了抵達既定的目標,不論是走哪一條路;波希米亞人深知如何在各種狀況下取得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不論是晴是雨,揚塵或是陰天,沒有什麼可以阻撓這些狂野的冒險家,他們天生具有辨別方向的本領。雄心壯志讓他們的思慮清晰,並對未來抱持衝鋒陷陣的高昂精神。生活所需是一道永遠的難題,而他們天馬行空的創造力總是能在困難真正發生前,輕而易舉地將之移開。他們有辦法逼小氣鬼掏出錢包,在梅杜薩之筏挖出松露;沒錢時他們可以活得像隱士一樣節制,但只要有一些財富落到他們手上,他們就會立刻沉淪至最具毀滅性的幻夢之中--追求最年輕貌美的女孩、喝最陳最好的美酒,好像他們的錢多到無處可花。然後,當最後一枚硬幣真正消失後,他們就再度回到過去的餐桌前,憑上帝的意思決定晚餐。他們會憑著一些技倆,接來各式各樣和藝術沾得上邊的工作,從早到晚辛勤得好像是專門尋找五法郎硬幣的某種動物。
波希米亞人穿著造形奇異的便鞋或破破爛爛的靴子,他們無所不知、無所不在。這天,他可能在裝飾華麗的會客室,靠著壁爐與人家聊天;隔天,他也許會出現在郊外露天舞會的樹蔭下乘涼。他們在林蔭大道走上十步,就一定會遇上朋友;而不管在哪哩,走三十步一定會碰上一個債主。
……
這就是波希米亞人的生活。社會上的道德之士對他們所知甚少、藝文界的保守人士攻擊他們;社會上的平庸者們找不到足夠的謊言和毀謗,去壓下波希米亞人的聲音和名字--他們已經憑著自己的大膽和天賦,摸索到了名望大廳的前廊。
這是一種極需耐心與勇氣的生活,一個人必須穿上最厚重的鎧甲,才足以抵抗愚蠢和忌妒者的攻擊,在路上,他必須緊抓著足夠的自信,才不至於時時跌倒。這是最迷人也最糟糕的生活,在故事裡有烈士、也有英雄,而一個人必須先認清所有無情的規則、並拋棄先前的自我,才有資格踏入波希米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