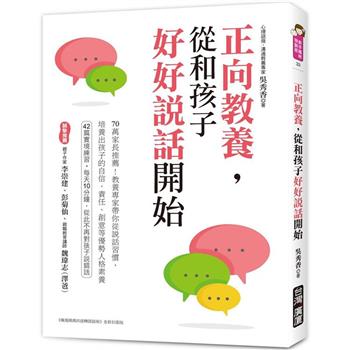序幕
我實在告訴你們,賣人子的人……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馬太福音》
他是歷史上最受憎惡的人物之一,那背叛了耶穌基督的門徒──加略人猶大。許多世紀以來,他的名字一直是背叛與欺騙的代名詞。
1970年代中期到晚期,埋藏超過1,500年的一份古老文獻在埃及的沙漠出土。一群埃及農民在尼羅河畔意外發現了一座洞穴。在聖經時代,這類洞穴是用以埋葬死者的。農民進入洞穴,想找尋古代的黃金或珠寶,隨便什麼可以賣錢的東西都好。黃金珠寶沒找到,他們卻在一堆人骨間發現了一個已開始碎裂的石灰岩匣子。盒內的東西出乎他們意料──那是一本神祕的皮革裝訂書,一部古書手抄本。不識字的農民無法解讀古老的文本,但他們知道古書在開羅的古物市場上可以賣得好價錢。這本書用的是紙莎草紙(papyrus),也就是古埃及的紙張。
這些農民完全不曉得,他們握在手中的是聖經考古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這份文件被「異端邪說」的標籤污名化,在1,800年前被宣告為邪書。
大約22年後的2000年4月,古物商費莉達•查克斯•紐斯伯(Frieda Tchacos Nussberger)在前往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途中接到驚人的消息。前不久她才從一名埃及古物商手中買下這部古老的手抄本,並將之攜往耶魯大學接受鑑定。現在透過手機,耶魯的手抄本專家彷彿投下了一顆震撼彈。「費莉達,太棒了!」他非常激動地說。「這個文件非常重要。我想它是《猶大福音》!」
對費莉達而言,這是多年追尋後的報償。雖然從不知道其內容,她卻早已對這部神祕的手抄本著了迷。真有可能是一部《猶大福音》嗎?
猶大故事的這個版本
對依勒內這類早期教會領袖來說是太具爭議性了。
奇怪的是,加略人猶大如此惡名昭彰,關於他的事實我們卻所知極少。他是耶穌十二使徒之一。他所來自的地方最有可能是猶太地(Judea),而不是耶穌和其他門徒所來自的加利利(Galilee)。猶大是十二使徒中管理錢財的司庫,根據某些福音書的記載,他也是耶穌最信任的盟友,這使他的背叛更顯可鄙。
即使關於猶大生平的細節混沌不明,他在歷史上的定位卻清楚明白。「他是出賣朋友的人。」新發現福音書的譯者之一馬文•梅爾(Marvin Meyer)解釋。「他是導致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人,也是永遠受詛咒的人。」在但丁《神曲•地獄篇》中,猶大被打入地獄最底層,被撒旦頭先腳後吞食。
「今天一般人心目中的猶大主要是耶穌的出賣者,一個背叛大業的人。」以早期基督教研究著稱的學者巴特•葉爾曼(Bart Ehrman)最近指出。「他們往往把他想成一個貪婪、愛財的人,對賺錢的興趣超過對他導師的忠誠。」
「這個字本身就受到鄙視。」威廉•卡拉森博士(William Klassen)進一步指出。「我想幾乎在整個西方世界,是連狗都不會取這個名字的。當然,還有在德國,將自己的孩子命名為猶大是違法的。」
基督和他的門徒都信守猶太教法,以今日的標準來說是正統派。但隨著時間過去,猶大陰暗的行為逐漸讓他們的整個信仰被認定帶有邪惡色彩。「傳統上在基督教的圈子中,猶大其實都與猶太人連在一起。」葉爾曼指出。「不只是因為他的名字,也因為他的特質在中古時代成為人們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他們是叛徒,貪得無厭,會背叛耶穌。當然,對猶大的這種刻畫也導致了幾世紀來可怕的反猶太行為。」
烙印在他名字上的污點所根據的是福音書中短短24行經文。正如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哲學教授史蒂芬•伊凡斯(C. Stephen Evans)所說:「加略人猶大鮮少出現在新約中,我想這是因為他是個羞恥。關於他的寥寥數語也非常陰暗,因此他被描繪得愈來愈壞,是個從錢囊偷錢的賊,甚至是個受到撒旦操縱的人。」
然而歷史記載,曾經還有另一個關於加略人猶大的文字資料來源。公元180年左右,在今日法國境內的一名教會領袖依勒內曾為文強烈抨擊一部題為《猶大福音》的希臘文本。「這部福音寫的是耶穌與猶大之間的關係,指出猶大實際上並未出賣耶穌,而是按照耶穌的指示所做,因為唯有猶大真正知曉耶穌所要傳遞的真理。」葉爾曼說。
猶大故事的這個版本對依勒內這類早期教會領袖來說是太具爭議性了。他們透過對它的譴責將之從歷史上抹滅,從此再沒人見過。
但「從此」是段很漫長的時間,而對這部福音的壓抑卻只能持續到它重新被找到以前。至少有一部抄本保存下來,在埃及乾燥的沙漠,黑暗無光的墓室中沉寂了近2,000年,直到它突然重見天日,並且在幾十年後由費莉達監管。
這部手抄本──猶太教-基督教考古中的一大發現──並未直接進入博物館,甚至連富豪收藏家的藏書室也沒進過。福音書從埋藏地出土只是一段詭祕旅程的開端。《猶大福音》被當成一件商品,在接下來的25年內於世界三大洲上輾轉求售,其內容僅在漫長的沉寂期間被瞥見幾次,貯藏狀況更距理想條件非常遠。旅程中的每一步都造成這份珍貴文件的狀況惡化,直到最後幾乎只剩下莎草紙的纖維碎片。
這份文件與其他三份文本裝訂在一起,發現者只知道它非常古老,而且很值錢。他們將抄本賣給開羅一名古物商,他也不懂古老的科普特文,但他知道這部抄本極有價值,只要能找對買家就好了。
埃及首都的潮濕空氣迥異於古抄本出土地的乾燥沙漠氣候,而濕氣,再加上炎熱,正是造成易腐物質毀損的重要因素。莎草紙文件就在古物商將它們以數百萬美元求售時逐漸朽壞。
接著,抄本被竊,到了歐洲──更準確說是瑞士,暴露在阿爾卑斯山的空氣中,毀損持續進行。抄本被留在銀行保險箱中腐壞,而這還不是最後一次。後來它們又由來自美國的專家鑑識,以確定其真實性。早在這個階段就已有人提出對文件毀損狀況的警告。學者希望透過妥善管理與提供適當的環境,以控制損壞情形,但那還要等好幾年。
古抄本接著因為出售有望來到了美國。紐約一位著名的手稿交易商又一次檢視了文件,可是對埃及賣方的要價與復原文件的花費有所顧慮,最後決定不買。失望之餘,開羅那名古物商最後將文件放在長島郊區的銀行保險箱裡,沒人知道文件的狀況,甚至沒人知道它們的存在。文件在那裡一放就是漫長的16年,繼續腐壞。
最後,費莉達終於將文件從銀行保險箱救出來,交由耶魯大學翻譯,有位學者也辨認出文本的主題和部分內容。有一小段時間,重要性已被發現的古抄本,似乎終於找到了歸處。然而費莉達曾說這個文本是「詛咒」,事實似乎也的確如此。猶大的污名在抄本發現後許久仍揮之不去,幾乎就彷彿文本不希望有人閱讀似地。
儘管這份文件收錄傳說中的《猶大福音》,耶魯大學仍擔憂可能牽涉的法律問題,不願購買。結果它被賣給俄亥俄州一名古物商。在短暫貯藏於冰箱冷凍庫期間,文件又進一步朽壞。
交易失敗讓手稿重回費莉達與瑞士的懷抱,終於找到一個環境條件可確保它們未來保存的歸處。脆弱的莎草紙這時已嚴重腐朽,稍加碰觸就有碎片掉落。不僅如此,學者還發現這些無價的文本有缺頁,可能是為了分別出售而撕去。
這段旅程的每一個階段都對手稿造成更多損壞。每一個階段都使愈來愈脆弱的莎草紙纖維變得更加惡化,古老文獻裡的更多字母和字、句面臨湮滅的威脅。旅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可能使從埋藏了數世紀的墳墓再次升起的加略人猶大之聲,被腐蝕損毀到再也聽不到。
猶大福音寫於13張莎草紙上,正反面都有──
有26個編有頁碼的書頁,從抄本的第33頁到58頁──
但是莎草紙已散落成數不清的碎片。
自費莉達從耶魯的專家口中得知神祕抄本的內容那一刻起,她就在與時間賽跑,要在書頁化為塵埃前找到有能力保存的買家。最後她將抄本交給位於瑞士巴塞爾(Basel)的「梅塞納斯古代藝術基金會」,這個基金會專門贊助古代文化或這類古物的考古研究計畫。她與梅塞納斯基金會共同請來世界上最傑出的科普特文譯者與學者之一魯道夫•凱瑟,因抄本即以罕見而古老的科普特文寫成。看到抄本損壞的程度後,凱瑟又找來出色的文件復原專家芙羅昂絲•達布赫(Florence Darbre)攜手合作。
2002年,達布赫在她位於瑞士的工作室首次打開裝有《猶大福音》的盒子。「我非得看看不可。我非得把盒子打開又關上數次不可。」她說。「要碰觸某些物品是需要鋼鐵般的膽量。」在她30年的工作中從未見過狀況這麼糟的古代文件。脆弱的莎草紙書頁已碎裂成數千片。「不論你復原的是什麼文件,背後總有段故事。你總會想,是誰寫的,它去了哪裡,誰曾擁有它,又有誰讀過它?」
為了尋找答案,凱瑟與達布赫展開了將碎片拼合的艱辛過程。這些碎片所訴說的故事曾經被早期教會領袖成功地打壓。但即使文件狀況如此殘破,其中仍有一行字亟待解釋,那就是以科普特文書寫的標題,Peuaggelion Nioudas──猶大福音。
這是歷史所巧設最複雜的謎題之一。猶大福音寫於13張莎草紙上,正反面都有──有26個編有頁碼的書頁,從抄本的第33頁到58頁──但是莎草紙已散落成數不清的碎片。如果一個碎片符合書頁的一面,還得符合另一面才行。凱瑟這樣說明了重建工作的艱鉅:「如果你把一份9至10頁的打字文件撕成許多小碎片,把一半的碎片扔掉,再試著把另一半拼湊還原,你就會明白這個過程有多困難。」
為了避免在非必要的時候碰觸文件本身,他們設計了一個極富巧思的辦法。首先,凱瑟利用碎片與書頁的照片尋找相合的碎片,接著再利用影本將碎片剪貼黏合。「每次我們找到一個碎片的位置,」他解釋,「我就把影本交給達布赫女士,由她將碎片放置在原件中。」接下來達布赫會試驗凱瑟的解讀是否正確。「我們一點一點摸索出抄本的文意,靠的就是這一次次的成功。」達布赫說。「拼合的碎片愈多,我們能解讀的愈多,揭露的故事也就愈多。」
另一位學者葛瑞格•沃爾斯特(Gregor Wurst)設計了一套可協助辨識莎草紙纖維的電腦程式,使碎片更容易彼此拼合。還有數百碎片等待拼合,但它們揭露的故事已是戲劇性十足。文本訴說的是耶穌基督受難前最後幾天的故事──這個故事可能會挑戰基督教最根深柢固的一些信仰。在這個故事中,叛徒成了英雄,而耶穌基督的受難乃是自己一手安排。文本與依勒內在1,800年前嚴加譴責的文件相符。其證據是耶穌將背叛的使命交付給猶大時所說,讓人不寒而慄的一段話:「你將受到所有其他使徒的詛咒。猶大,你將犧牲我的肉身。」
最早看到文件之一的美國學者史蒂芬•伊茂指出,「對很多人來說它帶有爆炸性,可能會引發信仰危機。」凱瑟教授進一步指出,「這確實是本世紀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它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是個真實的證據。」
尾聲
在<猶大福音>中,他所做的都是耶穌要求他的,他聽從耶穌,
始終忠誠。原來加略人猶大才是耶穌鍾愛的門徒、親愛的朋友。
──馬文•梅耶
<猶大福音>是一個獨特的故事,經歷過兩段充滿起伏的曲折歷程。第一段歷程在公元1∼4世紀之間,彼時基督信仰正從猶太信仰脫離出來。早期的基督信仰是一個多元的宗教,由於不同的信徒發展出相互競爭的觀點與信條,彼此競逐主宰地位。有些人將<猶大福音>稱為「失落的福音」,這份文本被發展中的教會烙上異端的印記,因為它不符合正統的政教議程,後來受封為聖人的主教依勒內更將之貼上「虛構故事」的標籤。到了公元4世紀,文本與其中對古老事件令人驚訝的說法,可以說已經從歷史上消失了。
到了現代,<猶大福音>則是經歷漫漫長路才重見天日。途中,文本飽受蹂躪,經歷人性的貪婪、欺騙和人與人之間的殘酷對待。它與其他文本一起被當作價值連城的商品進行交易──也曾失竊。這些過程不僅讓我們看到世間男女的脆弱,也看到人性普遍的不完美。
1984年,加布里埃爾•阿卜杜勒•薩耶德神父與漢納•阿薩貝爾和另一名埃及同伴,來到晨邊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峭壁上的哥倫比亞大學,請當時仍年輕但已聲譽卓著的古典學者羅傑•巴格納爾鑑定他們手中的文本。21年後,巴格納爾教授坐在他位於漢彌頓廳辦公室的電腦前,打開已掃入他的電腦,被稱為數學論文的那份文本。這也是路德維格•柯伊南教授22年前在日內瓦檢視過的文本,比巴格納爾初次見到文本還早了一年。
巴格納爾往下捲動文本,直到他在寫著希臘文的頁面上看到一個小小的標記,這個標記顯示,文本的來源與Pagus 6有關。巴格納爾手邊沒有地圖,但他指出倫敦國王學院的珍•羅蘭森(Jane Rowlandson)的一本書,《羅馬治下的埃及地主與佃農:Oxyrhynchite省的農業社會關係》(Landowners and Tenants in Roman Egypt: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Oxyrhynchite Nome),書裡有地圖顯示羅馬統治期間的埃及行政區。
Pagus 6是橫亙埃及Oxyrhynchite省的一條狹長地帶,朝馬加加的方向延伸。巴格納爾說明,Pagus 6是整合了早先在官僚體系下一些稱為小邦的一個區域,而在公元307或308年才成立。因此數學論文寫成的年代絕不可能早於其時,因為Pagus 6在那之前尚未出現。
這份論文及其他一起求售的古老莎草紙手抄本真的是同時發現的嗎?這樣的假設符合邏輯,但並非必然。有些證人聲稱這些文本是一起被發現,但證人也會訛誤,而且至少有一位涉及文本出土的關鍵人士已經不在人間。
即使文本確實在同一地點出土,每份文本仍可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收錄了<猶大福音>的手抄本,其創作時間可能比其他一起出土的文本都要早得多,更別提這是一份由更早的希臘文獻所抄寫的科普特文譯本了。
文本是隨何人一起埋葬?什麼樣的人會選擇與一份聖經文本、保羅書信、<猶大福音>與教導古代數學的文本一起下葬?為了解開種種與這部引人入勝的手抄本的疑惑,努力仍在進行中──而且勢將持續多年。
透過魯道夫•凱瑟以及芙羅昂斯•達布赫與小組其他成員持續不懈的努力,一部來自古老過往的文獻終能獲得重生,永遠嘉惠世人。狹小的書房裡,魯道夫教授坐在他的電腦旁,憶起他初次見到福音書的那一刻:「我所經歷的,是一個人面對謎團時慣有的反應。在我這一行裡,我們知道許多,卻也一無所知。我們時時會發現完全超越了先前藍圖的事物、理論與解釋,而我們必須願意改變我們對手抄本的看法。手抄本才是情勢的主宰。」
「這就好像我去拜訪一位陌生人,試圖聆聽他,但也明白我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了解他的靈魂深處……如果文本是完整的那會比較簡單,但文本中有許多空白。」
我們所知道的是,<猶大福音>是對基督信仰早期一份新穎而真實的見證。它的訊息顛覆了長久以來為人所相信,猶大出賣了他導師的說法,同時也讓我們所有人重新審視耶穌想要教導我們的事情。追隨自己的那顆星──這樣的觀念在今日與往昔同樣具有意義。與其放逐背叛者,或許我們應該更深入的自省,找尋我們內在的善。
未知仍在,充滿誘惑地等待著,等待我們在更了解一個新信仰誕生時去發現它。不論我們走得多遠,謎團似乎永遠存在。
出版後記
蘇黎世古物商費莉達•查克斯•紐斯伯在2000年購得收錄<猶大福音>的古抄本時,抄本已求售近20年,且從埃及先後流落歐洲、美國。瑞士的科普特文本專家魯道夫•凱瑟說他從未見過狀況如此糟糕的文本。「手抄本非常脆弱,輕輕一碰就會粉碎。」由於擔憂手抄本毀損的情況,查克斯將手抄本交給梅塞納斯古代藝術基金會進行修復與翻譯,最後將交給開羅的科普特博物館。手抄本計畫結合了考古學與最先進的科學,也是具有文化意義的主題,對國家地理學會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學會請來韋特史料研究所共襄盛舉,這是由Gateway電腦公司創辦人泰德•韋特(Ted Waitt)創始的基金會,目的在支持能透過歷史與科學探索增進人類知識的計畫。國家學會與韋特史料研究所將與梅塞納斯基金會共同鑑定手抄本,持續進行修復工作,並翻譯手抄本內容。但首先必須由修復專家芙羅昂斯•達布赫在科普特學者葛瑞格•沃爾斯特(Gregor Wurst)協助下將破損的文本重建起來。
書頁曾被人重新排序,而莎草紙書頁的上半部分(標有頁碼)也已脫落。更大的挑戰是像麵包屑般散落的近千片碎片。達布赫用鑷子夾起脆弱的碎片,放置在玻璃片之間。在電腦輔助下,她與沃爾斯特經過五年辛勞,總算成功重組了超過80%的手抄本。凱瑟與其他學者翻譯了長達26頁的手抄本,抄本中詳細描述了隱藏已久的諾斯底派信仰,早期基督教學者說這是數十年來最戲劇化的發現。凱瑟說:「這份文本能重見天日是個奇蹟。」
為了確認手抄本的年代與真實性,國家地理學會在不造成損害的情況下對抄本進行了最嚴格的檢驗。這包括讓細小的莎草紙樣本接受現有最嚴格的放射性碳定年,並與熟悉古文字學與抄本學的頂尖科普特學者進行諮詢。
2004年12月,國家地理學會派專人將五份微小的樣本送達位於土桑的亞利桑那大學放射性碳定年加速質譜實驗室。
有四份樣本取自抄本的莎草紙片,第五份樣本則是一小片皮革封皮,上面黏附著莎草紙片。過程中未損及手抄本的任何部分。
2005年1月初,加速質譜實驗室的科學家完成了放射性碳定年檢測。個別樣本的校正後年代互有差異,但整體的平均日曆年代在公元220年到340年之間,誤差範圍正負60年。
根據加速質譜實驗室主任提姆•朱爾博士與研究科學家葛瑞格•哈吉肯斯所說,「莎草紙與皮革樣本的校正年代數據極為集中,抄本的年代落在公元3或4世紀。」
自1940年代晚期發現以來,放射性碳定年就一直是從考古到古氣候學等領域中測定古器物與文物的黃金標準。加速質譜科技的發展更讓研究者得以就一件文物的許多微小碎片進行取樣檢測,手抄本的測年就是如此。
亞利桑那大學加速質譜實驗室的工作成果舉世聞名──包括《死海古卷》的精確定年,這也使得學者得以將古卷還原到正確的歷史脈絡中。
根據研究過手抄本的學者所說,抄本的內容與語言風格進一步佐證了其真實性。這些專家包括曾任日內瓦大學教授,也是《哈馬迪藏書》主要譯者之一的魯道夫•凱瑟博士;加州橘郡(Orange)查普曼大學(Chapman University)的馬文•梅耶;德國明斯特大學科普特學教授史蒂芬•伊茂。這三位對抄本的翻譯都功不可沒。
根據三位學者所言,抄本的神學觀念和語言結構與《哈馬迪藏書》中所見十分相似,《哈馬迪藏書》在1940年代於埃及出土,多數是諾斯底派文本,年代也落在基督教發展的最初幾個世紀。
「這個文本與我們已知的公元2世紀的思想相當一致。即使殘缺不全,文本仍非常耐人尋味──它與2世紀的某個時期極為符合。」梅耶博士說。
伊茂同意梅耶的觀點,認為抄本的內容反映出盛行於公元2世紀的獨特諾斯底派世界觀。「(若想假造這樣一份文本)你必須反映一個與我們今日所知完全相異的世界。這個世界有1,500年歷史……這樣的事即使是窮畢生鑽研這個領域的學者都很難了解,更別提憑空捏造了。只有真正的天才能創造這樣一份文本,而我個人認為這不啻是天方夜譚。」他說。
「我沒有絲毫懷疑,這個手抄本確實是近古埃及的文物,而且證據顯示,其中收錄的是貨真價實的古代基督教次經文獻作品。」伊茂進一步指出。
除了反映出諾斯底派的世界觀,古文字學的證據也可佐證抄本的真實性。科普特古文字學專家伊茂博士作了這樣的評估:「抄本由專業的抄寫者仔細寫成。這種字體讓我想起哈馬迪村的手抄本。字體與其中任何一部抄本中的都不是一模一樣,但卻是相似的字體。」
「對我來說,這樣一件物品有沒有可能是現代人仿製的問題根本不存在──想都不用想。你不只需要真正的材料,莎草紙──還不是隨便什麼莎草紙,而是要古代莎草紙,明顯有數百年歷史的老莎草紙──還要知道如何模仿非常早期的科普特字體。全世界有這份能耐的科普特專家沒幾位。你還得要能用科普特文寫一份文法正確而足以讓人信服的文本。能做到這個地步的人,遠比能閱讀科普特文的人數還要少。」
為了更進一步確保抄本的真實性,墨水樣本被送到以墨水鑑識分析聞名的麥克隆公司(McCrone and Associates)。分析結果再次證實了文本的真實性。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證實了墨水的主要成分是碳黑,結合劑則是一種樹膠──這與公元3、4世紀的墨水分析一致。
麥克隆公司另外使用一項稱為拉曼光譜學的技術,進一步確認了墨水含有某種金屬鎵(metal-gallic)墨水成份,與公元3世紀時使用的鞣酸鐵墨水一致。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誰吻了耶穌?:猶太福音出土千里追訪錄的圖書 |
 |
誰吻了耶穌?:猶太福音出土千里追訪錄 作者:賀伯.寇拉斯尼 / 譯者:胡宗香 出版社:秋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2-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76 |
二手中文書 |
$ 334 |
基督宗教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誰吻了耶穌?:猶太福音出土千里追訪錄
加略人猶大,歷代以來飽嚐憎恨,受盡唾罵,因為他是出賣耶穌基督的叛徒──那為了30銀錢背叛朋友之人。
但歷史也記錄了有關猶大的其他訊息。有一項記錄由極具影響力的教會領袖聖依勒內寫於公元180年,他在書中嚴詞抨擊《猶大福音》,因為這本書從這名墮落門徒的角度敘述了耶穌<
在世上最後的時日。在其書頁中,猶大是基督最鍾愛的門徒。
其中的敘述與歷代流傳下來的故事有著顯著不同,但自從被斥為異端後,《猶大福音》就逐漸消失,成為被歷史遺忘的文獻。直到現在。
在這本引人入勝又調查詳盡的報導中,作者賀伯.寇拉斯尼抽絲剝繭地敘述了《猶大福音》發現的過程,還有專家學者如何從古老的科普特文字中發掘出福音中隱藏了數百年的訊息。寇拉斯尼憑藉著一個調查記者與說故事高手的才華,追溯了被人遺忘的福音書跨越三大洲不可思議的旅程。
這趟旅程讓福音書經歷了國際古物買賣不為人知的世界,直到最後碎裂的莎草紙片終於吐露它驚人的祕密。
發掘《猶大福音》的歷程將是聖經考古上最偉大的偵探故事之一。
本書特色
◎隱沒1700餘年的《猶大福音》手抄本重見天日千里追訪錄。
◎繼《哈馬迪藏書》與《死海古卷》之後,被學者譽為20世紀早期基督教三大考古發現之一。
◎透過作者賀伯.寇拉斯尼的千里追訪、抽絲剝繭,本書儼然成為聖經考古史上最偉大的偵探故事與發現之旅。
◎史料價值與真實性超越丹.布朗小說《達文西密碼》。
◎重新定位猶大在基督教史上的歷史評價。
◎開啟聖經福音正典之外寬廣的思想之窗,重新認識耶穌的不同面貌。
◎宗教學家反思各宗教早期教義的最佳讀本;運用科際整合探究古物的精采典範;一場閱讀歷史新發現過程扣人心弦而愉悅的經驗。
章節試閱
序幕我實在告訴你們,賣人子的人……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馬太福音》他是歷史上最受憎惡的人物之一,那背叛了耶穌基督的門徒──加略人猶大。許多世紀以來,他的名字一直是背叛與欺騙的代名詞。1970年代中期到晚期,埋藏超過1,500年的一份古老文獻在埃及的沙漠出土。一群埃及農民在尼羅河畔意外發現了一座洞穴。在聖經時代,這類洞穴是用以埋葬死者的。農民進入洞穴,想找尋古代的黃金或珠寶,隨便什麼可以賣錢的東西都好。黃金珠寶沒找到,他們卻在一堆人骨間發現了一個已開始碎裂的石灰岩匣子。盒內的東西出乎他們意料──那是一本...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賀伯.寇拉斯尼 譯者: 胡宗香
- 出版社: 秋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2-01 ISBN/ISSN:986712017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哲學宗教> 基督宗教
|